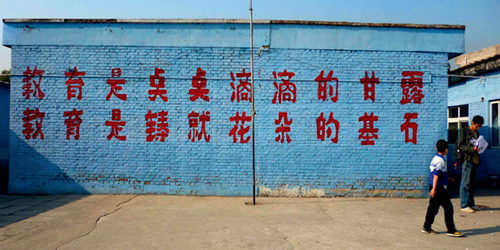李淼
戶籍制度形塑了城鄉教育的機會壁壘,跟隨農民工父母來到城市后,流動青少年因持有農村戶籍很難進入城市公立學校就讀。1990年初,打工子弟學校(又稱民辦簡易學校)開始在中國城市地區雨后春筍般涌現,填補了這一教育市場的空白。在此后的很長一段時間里,許多打工子弟學校并未能獲得當地教育行政部門頒發的辦學許可證,處于國家教育體系之外的灰色地帶。但是,由于這些學校在保障農民工子女受教育權利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被政府所默許,并且得到了社會各界的認可和贊揚(Kwong,2004)。然而,以營利為終極目的的辦學模式衍生了一系列問題,嚴重危害了流動青少年的學業成績和社會性發展(Chen & Liang, 2007; Lu & Zhou, 2013)。在打工子弟學校利弊爭議不休的背景下,近年來城市戶籍人口出生率的降低,迫使公立學校不得不面對生源嚴重不足的局面,同時為緩和社會上日漸迫切的教育公平訴求,不斷有新的教育舉措出臺,承諾將流動兒童安置到就近的公立學校中,結果使很多打工子弟學校被迫逐步退出流動人口教育的供給市場,少部分學校則通過政府購買學位而獲得了合法辦學資格。
在審視流動青少年的受教育經歷時,以往研究多關注諸如打工子弟學校物質條件窘迫,師資力量薄弱等外顯要素對延續學生邊緣化的社會地位,和不平等教育境況的助推作用,卻極大忽視了貫穿于學校教學過程始終的隱性文化特征。與此同時,流動青少年自己的聲音也被社會再生產的宏大敘事所淹沒,被界定為制度安排的逆來順受者或盲目的反抗者。基于筆者對S市一所打工子弟學校為期一年的田野調查和持續關注,本文聚焦流動青少年日常學校教育經歷中的文化要素,以及他們對受教育權利的認知與批判。通過細致剖析“素質評價”和“勤奮決定論”這兩個學校文化的主線,筆者試圖從意識形態層面理解社會階層結構的再生產是如何經由社會、學校與個體之間的持續互動得以實現的。
素質評價:社會階層觀念的灌輸
1999年,基于對流動人口義務教育市場供不應求的判斷,陸校長與妻子創辦了一所名為“綠樹學校(化名)”的打工子弟學校。17年后,該校的學生人數已由創建初的十幾人增長至800多人,教職工也由最初的“夫妻店”模式增加至40多人。在市郊,綠樹學校緊挨著一個舊貨市場,學校門口整日聚集著來往嘈雜的人群,周圍是一排排外來人口租住的簡易民房。伴隨著打工子弟學校辦學政策的調整與變動,綠樹學校在與當地教育行政部門的艱難角力中曾有五次被取締和一次被關停的經歷。精于變通的陸校長用舉校搬遷的辦法成功化解了學校被取締的危機,在面臨被關停的考驗時,他又借助多年積累的人脈注冊了一所具有課外輔導資質的武術學校,并通過虛假宣傳逐年擴大招生,將其發展成為一所九年制義務教育學校。2014年,綠樹學校終于告別了15年的非法辦學狀態,獲得辦學許可證,這個身份轉變為學校帶來了更有力的政府支持和更豐厚的社會捐助。在接待各級領導和愛心人士的報告會上,陸校長曾多次動情地提及當年辦學的初衷:提高農民工子女素質,改變城市人對農村人的刻板印象。然而,他深知一紙辦學許可證并不能確保打工子弟學校擁有一個平穩繁榮的未來——營利始終是他在各種現實考量和權衡利益之后的堅定選擇。
在營利目標的驅使下,綠樹學校實際上并沒有為提高流動青少年的素質教育作出多少現實努力,相反,在學校教與學的過程中,彌漫著對流動人口低素質的歧視性評價。這種評價將流動青少年界定為“沒法教”和“教不會”的頑劣學生。一方面,學生對此評價的反感和抗拒使“自我實現預言”成為現實,另一方面,它催生了契合學生低素質的,量體裁衣式的教學模式和師生互動形式。筆者在調研中訪談了六名八年級教師——他們情緒激動地痛斥學生是不折不扣的“混混”,視學校為“幼兒園”和“收容所”。實際上,這些同樣出身農村的民辦教師大多離家多年,對今日農村留守兒童的境況和心態所知寥寥。即便如此,他們無一例外的把流動青少年看作全國兒童素質評價體系中的最差生。在他們眼中,流動兒童不如城市兒童,缺乏城市中產式的家庭教育,道德敗壞、縱容享樂、不思進取;他們也不如農村兒童,在城市不良風氣的熏陶下不再單純善良、知足感恩。談到學生未來的就業前景,陸校長篤定地說:“其實,來到這所學校以前,他們就只想像他們的父母那樣在北京繼續生活,有的跟父母去賣菜,有的走街串巷安裝空調。他們沒有上進的動力,整天想的都是那些‘男盜女娼’,這些孩子放在我這我也是沒辦法(管)。”
對學生素質低下的評價指導著綠樹學校的課堂教學、成績考核和師生互動。既然流動青少年知識基礎薄弱、學習動機不強、課堂紀律差,教師們就順理成章地選擇了十分松散的授課方式,整天讓學生們抄寫板書或做習題,成績考核也非常寬松。不僅允許學生作弊,甚至會在考試過程中泄漏答案。這樣的授課和考核方式在打工子弟學校中并不是什么羞于啟齒的事情。相反,它們鑄就了陸校長們眼中的“雙贏”:好成績讓學生對家長有交代、免于責罰;也讓家長滿意,相信獲得了與付出的學費相襯的回報。然而,受學生素質低判斷的預設影響,實際的師生關系非常緊張。在課堂上,教師與學生之間經常發生激烈的言語沖突,教師咒罵學生混吃等死,學生則情緒失控大喊大叫,有時甚至會發生身體沖撞,這時總是以陸校長出面制止、威脅學生將被學校開除收場。
作為學生,流動青少年雖然也覺察到歧視性的“素質評價”正塑造著他們日復一日的學校經歷,但他們卻也通過“素質評價”的邏輯來批評父母、教師和陸校長,并以此認識自己所身處的生活世界。外來務工者向綠樹學校繳納了在他們看來不菲的學費,購買義務教育機會,而基于此形成的家長與學校之間類似“顧客–廠商關系”的關系使前者對后者充滿了敵視情緒。筆者經常聽聞家長譴責教師不負責任,質問陸校長的所作所為能否對得起自己收的學費。在筆者調研時,曾目睹家長們由于對教學質量的不滿,與同鄉眾人圍堵校門威脅要毆打教師,并向陸校長討要誤工費和精神損失費。學生們并不贊成父母的做法,他們經常用“他們素質低”這樣的回答來應對筆者對類似事件的追問。家長對教師的指責也進一步加固了教師對學生素質低下的判斷,而學生們卻認為教師才是他們身邊素質最低的人,因為他們承受著教師的歧視言語,有的學生甚至還遭受體罰。在這個市郊的破敗社區里,精于人情、人脈眾多的陸校長卻是大多數學生公認的素質最高的人。盡管學生們曾向筆者透漏陸校長有侵吞公益捐贈的行徑,但他們仍舊羨慕校長有車有房,比社區里的很多人有錢。
在綠樹學校,流動青少年的所有經歷都緊緊圍繞著與其素質相關的評價。他們無奈地承受著強加的歧視,以及基于這些評價實施的課程教學和成績考核。“素質評價”將人們按照素質的高低區分為優劣有別的不同群體,其實質是認同當前社會階層分化的現狀,并承認其合理性。綠樹學校的教師們通過自己的言行舉止將這種社會階層分化的觀念灌輸給學生,并使他們學會了用素質標準評價別人,從而認識自己所處的階層地位。當然,“素質評價”主導著綠樹學校的日常實踐邏輯絕非偶然——長久以來,提高人口素質是中國人口政策和教育政策的首要目標,用素質高低劃分社會階層是公眾意識的核心。
美國學者安德魯· 基普尼(2006)指出,要理解中國社會,“素質”是無可替代的關鍵詞。一方面,從控制人口數量到提高人口素質,對“質”而非“量”的強調說明了中國國家發展戰略的調整。另一方面,政策制定者和政治精英們促進了“素質”的世俗化,使它從政策領域進入了公眾的日常話語,并跨越了先天遺傳和后天培養的二元對立,成為衡量一個人全部能力的神圣標準。在當前社會轉型的過程中,社會各階層正經歷著分化、重組和整合,素質為持續變動的社會結構提供了穩定的衡量標準。逐漸地,關于素質的意識形態控制了社會的全部領域,這種控制便于治理一個受不平等和高度競爭所困的中國社會(Anagnost, 2004)。作為一個自上而下的意識形態工具,“素質評價”及其話語固化了階層邊界,規制著社會階層間的流動,并使社會流動日趨剛性和僵化。上文綠樹學校的日常教學實踐正是基于這樣一種認識:底層學校對素質提升無能為力。這樣的學校教育徹底淪為了社會再生產的機制,極大地阻礙了底層青少年的向上流動。流動青少年對“素質評價”的順從和認同更加劇了自身的困境,使其抗爭難以突破社會結構的限制。
勤奮決定論:社會流動的烏托邦
卡兒· 曼海姆(2009)在其著作《意識形態與烏托邦》一書中對意識形態和烏托邦的知識社會學意涵作了精當的分析。他指出,作為知識的兩種特殊形式,意識形態和烏托邦都是對現實的曲解:意識形態有助于維護現存秩序,烏托邦則是為顛覆現存秩序時對未來的非理性憧憬。在綠樹學校,作為一種意識形態,“素質評價”合理化了社會上對流動人口的階層定位,塑造了流動青少年的階層觀念并將其嵌入社會再生產的敘事邏輯中。與之相輔相成的是,只要憑借自己努力就能取得成功的信念孕育出了一個關于社會流動的烏托邦。這個烏托邦不僅全然否定了外在結構要素的支配作用,而且,由于它過分強化了流動青少年的主觀能動性,實質上是認同和支持社會達爾文主義,這樣必然會使他們陷入更加弱勢的地位。
筆者在綠樹學校的所見所聞徹底顛覆了以往對打工子弟的印象。在新聞鏡頭前,他們是勤奮學習、志向高遠的學生,即使阻力重重也絕不放棄;在紀錄片里,教室里回蕩著朗朗的讀書聲,操場上是一張張如花的笑臉。然而,這一切都很難在綠樹學校中找到痕跡。七、八年級的學生們極度厭倦枯燥乏味的學校生活,只有在媒體采訪時才會勉強配合、裝裝樣子,平常都是混一日算一日的架勢。幾個學生抱怨到,要不是家長“威逼利誘”,根本沒人愿意上學,早就想輟學去打工了,打工既能掙錢又能擺脫管束。被公立學校“下放”到綠樹學校的一位支教老師對此嗤之以鼻。她列舉了幾個寒門出貴子的例子,總結道:“這樣的家庭狀況必須得自己努力,要不別想走出這垃圾堆(指社區)。”
“勤奮決定論”是綠樹學校全體師生虔誠信仰的成功法則,其邏輯簡單直接,按陸校長的話說:“在拼爹的社會無法拼爹,勤奮是他們沒有選擇的選擇。”綠樹學校中也有勤奮用功的學生,但尋找這樣的學生不能按考試成績等顯性指標。七年級的一個英語教師認為,綠樹學校的考試紀律渙散,所以成績好的未必是好學生;真正的好學生上課聽講,作業按時完成,雖然他們也會抄襲,但心態上起碼是想要學些東西的。在校長辦公室,筆者看到了幾張學生與陸校長的合影。照片中的學生是各年級評出的學習奮進獎得主,其中有三個人還獲得了國內外公益組織頒發的助學金。然而,隨著年級的增長,越來越難評選出優秀生了,一方面,學生人數隨年級上升急劇遞減,一年級時的50多人到八年級時只剩下七、八個人。面對著無法在北京就讀高中和參加高考的殘酷現實,很多學生無奈之下回到了農村老家,還有一些進入了北京地區的職業學校或干脆輟學打工。另一方面,對學業前景的悲觀預見使留下來的學生早就失去了努力學習的動力。他們將注意力轉移到了戀愛和結交朋友上,學習成績說得過去就好。
陸校長和教師們堅稱流動青少年們糟糕的學習狀態與該校的學習環境和教學水平并沒有什么關系,其主要根源是學生的懶惰,這恰恰是流動人口素質低下的集中表現。有趣的是,在否定綠樹學校對學生學業發展負面影響的同時,卻沒有一個教師情愿讓自己的孩子在綠樹學校上學。與公立學校屢次交涉均告失敗后,大多數教師將孩子送回了農村老家,極少數人抱著觀望的態度把孩子留在身邊照顧。陸校長把自己的兩個孩子送入了北京的一所公立小學,為此還“自愿”繳納了幾萬元的贊助費。
流動青少年們也將學業失敗歸因于自己不夠勤奮。在與筆者的交談中,他們敏銳地感知到了生活中的諸多不利因素,如家庭教育的缺失、綠樹學校及其教師們的不負責任,以及來自輟學的干擾,但最后他們都將主要原因歸結為自己不夠努力,并為此感到失落和羞愧。久而久之,綠樹學校對責任的推卸與學生的自我歸因相互印證,將學校和社會對流動青少年學業失敗的責任轉嫁給了學生本人。
其實,學習不夠勤奮努力的自我歸因并不完全導致流動青少年對現實的沮喪,相反,這種歸因使他們更加堅信自己總有機會憑借勤奮獲得成功。這種信念為他們編織了一個關于社會流動的烏托邦。即使在物質環境和教學水平都無法與公立學校相提并論的綠樹學校里,他們也能自由地暢想未來。學生們對筆者承認,無論從哪個方面說,綠樹學校都不如附近的任何一所公立學校。在北京本地生源不足的壓力下,近幾年來,附近的公立學校開始接收流動青少年,但后者需提交五證[1]等諸多相關手續才能入學。由于入學手續相當復雜,加之相信勤奮是超越一切外在條件的成功要素,許多學生們主動放棄了進入公立學校的機會,認為無論在打工子弟學校還是在公立學校上學,只要勤奮學習,改變境遇的希望一直都在。但實際上,他們并沒有將勤奮決定論付諸實施,這個學校和學生共同建構的烏托邦帶給他們的僅僅是心理安慰和寄托。
與此同時,更多學生并不認為公立學校比綠樹學校好。為爭奪生源,打工子弟學校與公立學校展開了惡性競爭。前者經常詆毀后者實力不足、徒有其表,這使很多流動青少年形成了對公立學校的不信任感。當筆者問到不選擇公立學校的原因時,學生們擺出了幾條陸校長經常掛在嘴邊的理由:公立學校硬件好、軟件差;教師不負責任、作業多、為了芝麻大點小事就找家長。在一次電話訪談中,陸校長概括了他對公立學校的看法:“在接收打工子弟這件事上,公立學校跟我們的態度是不一樣的。他們滿腹牢騷,就像下嫁了一樣。他們不愿意收打工子弟,可又沒辦法,就像后媽養繼子。我們(打工子弟學校)才是親媽!”
簡言之,“勤奮決定論”是流動青少年寄希望于憑借刻苦學習就能實現向上流動的美好憧憬,但現實情況極大地偏離了這種社會流動的理想類型。素質話語和素質評價構筑了一個充斥著階層差異的現實世界,單獨個體的成功流動難以逾越其根深蒂固的結構性障礙。曼海姆指出,意識形態與烏托邦相互滲透、彼此影響。在“勤奮決定論”的鼓舞下,流動青少年渴望能夠弱化以素質為標準分化的階層差異;在“素質評價”的灌輸中,他們認識到勤奮可能是改變社會階層地位的可行方法。而實際上這兩者卻在綠樹學校教學實踐中彼此協同作用,不斷加劇著流動青少年的邊緣化。
權利意識的萌生:順從抑或抗拒?
在近期的政策調整過程中,以北京市為例,已取締和關停的打工子弟學校就有100多所,其目的是“改善流動人口的受教育環境”。據粗略統計,北京約40多萬名流動兒童(約占北京市流動兒童總數的80%)被分流至公立學校,而仍有近9.5萬名兒童在130多所打工子弟學校就讀。在未來的一段時期內,打工子弟學校將繼續為流動人口提供在城市中的受教育機會。當學者們紛紛為公立學校吸納流動青少年獻計獻策時,筆者卻在調研中發現:即便有機會進入公立學校就讀,很多學生仍選擇繼續留在打工子弟學校。綠樹學校的學生將勤奮決定論奉為精神寄托,堅信逆境不礙出人才。但盡管如此,學生們還是認識到了教育經歷中的消極方面,這些反思促進了其教育權利意識的萌生。
在班會上,流動青少年針對“受教育權利”問題展開了激烈的討論。他們歷數到:教師們上課心不在焉、辱罵甚至體罰學生;陸校長吞占公益組織和好心人募捐的財物;學費和伙食費持續上漲;學校和教師幫助學生考試作弊,不過是自欺欺人??綠樹學校為他們提供的教育是要付費的,而教學質量遠遠比不上城市公立學校和鄉鎮地區學校。深究原因,學生們將批判的矛頭對準了綠樹學校的營利性質和此類打工子弟學校普遍存在的管理混亂現象。據此,他們斷定自己并未享有課本上所說的平等的受教育權利。
然而,因教育權利喪失產生的不滿并沒有引發更激烈的情緒,“勤奮決定論”在很大程度上緩解了流動青少年因被剝奪感衍生的負面情緒。筆者追問學生們對公立學校入學難的看法,很多人淡然地說已經“想開了”,只要踏實勤奮,無論是通過學業成功還是在市場上打拼,都能在城市中立足。當得知農村戶籍身份學生無法在北京參加高考時,幾個渴望接受高等教育的學生坦言自己起初非常憂郁,決心輟學打工。但是,當他們聽說親戚家的哥哥姐姐們回到農村后刻苦學習,順利考上了重點高中,又給了他們莫大的鼓舞。
面對學校和社會加諸的重重障礙,流動青少年在日常生活實踐中的回應是順從還是抗拒?美國學者Solorzano和Bernal(2001)歸納了教育場域中弱勢群體學生的四種行為類型,包括反動行為(reactionary behavior)、順從型抗拒(conformist resistance)、自食其果型抗拒(self-defeating resistance)和變革型抗拒(transformational resistance)。雖然這四種行為類型無法涵蓋全部學生行為,但對它們進行細致的說明能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學生行為與社會結構之間的辯證關系。據Solorzano和Bernal(2001)的解釋,反動行為指學生因一時的樂趣得不到滿足或受沖動驅使而抗拒學校中的一切,但這種行為本質上不會對權力格局構成威脅。當學生通過學業成功等順從主流社會價值觀的方式實現向上流動時,這種行為結果顛覆了社會再生產的刻板印象,因此被稱為順從型抗拒。需要指出的是,無論是反動行為還是順從型抗拒,這兩種行為都不以對教育邊緣化社會根源的反思和批判為前提,也就無法對社會再生產的整體進程施加任何實質性的影響。文化研究經典著作《學做工》描寫了一群英國工人階級白人學生的“反學校”行為,屬于自食其果型抗拒。這些英國學生反抗教師權威、諷刺學業成績好的同齡人、貶低腦力勞動的價值,終日游蕩在學校里混日子和找樂子(威利斯,2012)。他們部分地洞悉了學校教育的本質是與社會合謀再生產底層階級,而不是幫助寒門子弟出人頭地,因此選擇了這種自暴自棄的行為。也因為他們選擇了自暴自棄,所以無力扭轉社會再生產的進程。只有當學生明確地意識到教育的再生產本質,并以改善自身所屬群體的社會地位而奮力實現向上流動時,才有希望改變不平等的境況,這種行為即變革型抗拒。
在分析流動青少年的行為特征時,學者們傾向于將其歸入“自食其果型抗拒”,認為他們建構了類似于《學做工》中英國白人學生的“反學校文化”。筆者認為簡單地套用西方概念難免有失偏頗。基于Solorzano和Bernal提出的行為類型學,判斷流動青少年的行為模式需要考察兩個前提:第一,他們是否洞悉了教育的再生產本質;第二,他們實現向上流動的動機是不是改善所屬群體的邊緣化境遇。
首先,在綠樹學校,流動青少年的批判從未觸及教育的再生產本質。他們早已厭倦了單調無趣的學校生活,于是自發地批判周遭的一切:陸校長的唯利是圖、教師的懈怠教學、學校管理的混亂和嘈雜無序的社區。在這種憤懣的情緒中,他們看到了自己未來的出路:進入北京地區的職業學校,或者畢業后去打工。對此,他們感到灰心失望卻又難以用行動改變現狀。然而,即使高等教育對流動青少年來說遙不可及,他們仍確信學業成功是實現向上流動的有效方式(周瀟,2011)。在訪談中,有些學生用大學生找不到工作的例子來否定教育的社會流動功能,但他們卻都為自己的學業失敗感到羞愧,這使他們的否定更像在尋找心理安慰。
其次,雖然流動青少年非常珍視與同輩群體的友誼以及由此獲得的歸屬感,但他們談論和評價社會問題時沒有群體觀念(史秋霞、王毅杰,2015)。更準確地說,游走于城市和農村之間的生活狀態使他們很難認同和界定自己究竟屬于哪個社會群體。據此,筆者認為流動青少年的批判和抗拒沒有涉及教育的再生產本質;他們的群體意識薄弱,即使渴望向上流動,也主要是為了改善個體的生活境況。因此,Solorzano和Bernal歸納的四種行為類型都不足以概括中國流動青少年的行為特征。
根據筆者的調查,流動青少年的行為是矛盾復雜的、似是而非的,這是由于他們沒有看透其教育邊緣化的深層次社會根源。比如,他們厭惡教師的辱罵,卻又理解其苦衷;他們痛斥綠樹學校的營利本性,卻又贊揚陸校長是事業成功者。在“素質評價”和“勤奮決定論”的合力作用下,流動青少年在順從和抗拒之間左右徘徊。“素質評價”灌輸了階層觀念,他們順從于意識形態并使用它去認識社會結構,但卻在此過程中遭遇了歧視和不公,并由此導致了不滿和抗拒。“勤奮決定論”給了他們向上流動的希望,使他們安于順從制度的安排。因此中國流動青少年的行為可以大致概括為,順從中孕育著抗拒,抗拒中潛藏著順從。
余論:不在場的階級意識
長久以來,馬克思主義階級理論引導著我們對社會階層關系的認識和分析,它將不平等的生產資料占有制度視為勞動者被剝削和異化的根源,認為當勞動者擁有階級意識時,他們即具有了與他者相區別的自我意識和群體凝聚力,進而能訴諸行動,改善自身境況。筆者的研究發現,流動青少年在順從與抗拒之間左右徘徊,對事物的批判和反思多聚焦零散細碎的問題,沒能看透教育的再生產本質,因此他們沒有形成階級意識。由于不斷變動的生活和戶籍制度塑造的教育困境,流動青少年是一個較為松散的社會群體,“既不屬于這里,也不屬于那里”。學校教育內容也直接瓦解了有望形成的階級意識。關于素質的意識形態讓學生認同社會階層結構,同時,勤奮決定論又使他們追求向上流動的手段和方式被規制在了制度安排的框架之內。
調研結束后,筆者仍與綠樹學校的流動青少年們保持著密切的聯系,他們都沒有拿到初中畢業證,[2]直接進入了京郊的勞動市場。出乎筆者意料的是,他們經常為了追求更優厚的薪資待遇、更便捷的交通,或者是更公平有序的工作環境而頻繁跳槽,這恰恰是第一代農民工很難或不敢去做的。Woronov(2011)也曾撰文指出,在用工荒普現各地之時,流動青少年的市場能力表現為能夠對他們不滿意的工作說不。從某種程度上說,馬克斯· 韋伯對市場地位和市場能力的分析似乎更能解釋這個現象。無論流動青少年是否具有階級意識,他們的市場能力都是不可忽視的,這將使他們成為中國經濟市場上的重要力量。至于市場過程將如何影響該群體的行為模式和權利意識,則有待進一步關注和考察。(文中人物、地點皆為化名)
(作者單位:山東大學哲學與社會發展學院)
參考文獻:
[1]保羅·威利斯:《學做工:工人階級子弟為何繼承父業 》,江蘇譯林出版社2012年版。
[2]卡爾·曼海姆:《意識形態與烏托邦》,姚仁權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年版。
[3]史秋霞、王毅杰:《片面洞察下的“反學校”生存——關于教育與階層再生產的探討》,《華東師范大學學報》2015年第3期。
[4]周瀟:《反學校文化與階級再生產:“小子”與“子弟”之比較 》,《社會》2011年第5期。
[5]Anagnost, A.,“The Corporeal Politics of Quality (Suzhi)”,Public Culture, 16(2004).
[6]Chen, Y., & Liang, Z.,“Educational Attainment of Migrant Children: The Forgotten Story of China’s Urbanization”, In E.P. Hannum, (ed.), Education and Reform in China. New York: Routledge,2004.
[7]Kipnis, A.,“Suzhi: A Keyword Approach”, The China Quarterly, 186(2006), pp. 295?313.
[8]Kwong, J.,“Educating Migrant Children: Negotiations between the State and Civil Society,” The China Quarterly, 180(2004).
[9]Lu, Y., & Zhou, H.,“Academic Achievement and Loneliness of Migrant Children in China: School Segregation and Segmented Assimilation”, Comparative Education Review, 57(2013).
[10]Solorzano, D. G., & Bernal, D. D.,“Examining Transformational Resistance through a Critical Race and Latcrit Theory Framework: Chicana and Chicano Students in an Urban Context”, Urban Education, 36(2001).
[11]Woronov. T. E.,“Learning to Serve: Urban Youth, Vocational Schools and New Class Formations in China”, The China Journal, 66(2001).
注釋:
[1]“五證”指家長或監護人在北京暫住證,在京實際住所居住證明,在京務工就業證明,戶口所在地鄉鎮政府出具的在當地沒有監護條件的證明,和全家戶口簿等五種證件。
[2]2014年以前,綠樹學校沒有當地教育行政部門頒發的辦學許可證,因此無法為畢業生發放畢業證。很多學生、家長和教師們對此并不知情,這也是陸校長在招生時蓄意隱瞞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