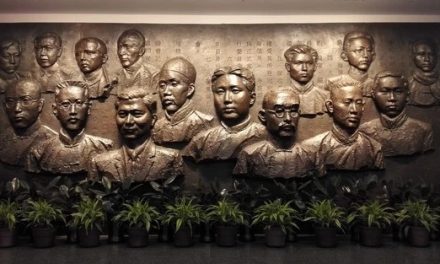楊成
自古至今,對于任何國家的政治與政府來說,沒有什么政治功能以及與之匹配的制度安排比領導人更為重要。正是他們在事實上制定著所在國家內政外交的大政方針,從而在相當程度上內在地決定了本國的發展路徑。作為政治家,能夠擁有足夠的政治權威、獲得相對自主和獨立的執政空間是每個領導人孜孜以求的目標。換言之,強人政治和政治強人本就是一體兩面。
新世紀以來,強人政治和政治強人作為話語、敘事以及現象出現的頻率明顯增加,甚至有學者認為世界政治正在進入強人政治的新時代。這其中,最為引人注目的大概是俄羅斯總統普京。相較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和新一輪歐盟復合型危機后涌現的一批以民粹口號為包裝、以保護主義為內核的政治強人,2018年3月18日再次順利高票當選為俄羅斯總統的普京無疑是新時期強人政治的神話。僅居高不下的民意支持一項,就足以讓熟悉了民主政治運行邏輯的西方領導人滿懷羨慕、嫉妒但又無法恨的復雜情緒。
但對普京而言,第四任總統任期的序幕剛剛拉開,2024年任期才結束的他已經注定是上個世紀以來繼斯大林之后執政時間最長的俄國領導人。那么,普京的政治新周期到底是如何發生的?未來它又將呈現怎樣的基本面貌?俄羅斯在普京的長期執政中獲得了哪些歷史性機遇?俄羅斯在政治強人普京的持續統治中會迎來“至暗時刻”,還是重新崛起為俄羅斯人念念不忘的全球大國?當我們探討普京治下的俄羅斯的發展情境時,這些問題都應被反復審視。
俄羅斯強人政治的歷史傳統傳承與現實制度安排
偏好強勢及有個性的領導人是俄羅斯政治文化的一大特色。這一傳統貫穿于整個莫斯科公國及帝俄時期,絕對君主制與東正教相得益彰,后者有別于強調個人、自由和民主的西方基督教文明,更多強調使命感、責任感,這導致指稱法律與力量的“沙皇”一詞連同其背后的強人政治邏輯代代傳承。
1917年的“十月革命”砸碎了帝國主義鏈條上最薄弱的環節,并從此開始了影響全人類的偉大的社會主義建設實驗,但這并不妨礙政治強人崇拜和強人政治邏輯從歷史的深處滲透進蘇維埃的政治基因中。在1924年列寧去世后,斯大林借助總書記的身份經過幾番政治權力斗爭,最終確立了蘇共無可爭議的絕對領導地位。政治強人斯大林的強人政治一直延續到1953年去世為止,總共將近三十年。隨后,赫魯曉夫依靠對斯大林個人崇拜的公開批判,建立起新的政治周期,集體領導原則重新獲得確認,但在實際操作中赫魯曉夫又不可避免地滑向了新一輪政治強人的歷史建構進程中,直至1964年10月被黨內力量予以罷免。赫魯曉夫出局后,蘇共曾嘗試以書面形式防止強人政治的再現,但隨著“三駕馬車”中勃列日涅夫的權威日增,蘇聯政治最終還是回到了歷史的路徑依賴之中。安德羅波夫和切爾年科短期過渡后,戈爾巴喬夫以改革派身份接過明顯僵化、老化的蘇聯政治馬車。在經歷多次嘗試體制內改革但都未能取得如期成效后,戈爾巴喬夫將話語目標更多轉向了民眾,試圖利用社會底層的支持取得改革、重建社會主義的正當性。歷史節奏出現了驚人的重復,但同樣青睞強人政治的戈爾巴喬夫未能真正變成政治強人,最終葬送了蘇聯和蘇共。
蘇聯解體后,俄羅斯開始在葉利欽團隊的帶領下采取制度移植的路徑,試圖在最短的時間內實現從威權到民主、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新一輪現代化轉型。但這一復雜程度不下于社會主義建設的歷史過程,恰恰是以民主的名義而以強人政治的實質予以推進的。由此,俄羅斯強人政治的傳統和現實政治中的超級總統制等制度安排構成了嚴密的耦合關系。
1993年12月12日,葉利欽贏得了至關重要的府院之爭的政治勝利,他所主張的以總統為絕對優先的憲法制度設計獲得了全民公決的支持。在公民投票之前,葉利欽攜80年代末90年代初大轉型中積累起來的領袖群倫的群眾基礎,呼吁俄羅斯民眾支持他的憲政法案。這一段演講說出了強人政治的制度安排對葉利欽這個政治強人的緊迫性和重要性:
我并不否認在憲法草案中總統權力的確非常可觀,但是你們還想看到什么呢?這是一個沙皇和領主們長期統治的國家,一個集團利益沒有得到充分發展的國家,一個上述利益的代言人沒有清楚界定的國家,一個正式的政黨才剛剛誕生的國家,一個紀律性不強、人們漠視法律的國家。在這樣一個國家,你們能僅僅依賴或主要依靠議會嗎?如果是這樣,那么用不了半年,如果不是更快的話,人們就需要一個獨裁者。我敢保證,可以找到這樣一個獨裁者,而且很有可能就在同一個議會里??這不是一個關于葉利欽的問題,而是一個關于人民的問題。人民需要一個官員,他可以對人民提出的要求做出答復??(在新憲法中)俄羅斯總統需要足夠的權力使之能夠改革這個國家。
最終,當時的俄羅斯民眾選擇了信任葉利欽,也就意味著葉利欽有關強人政治的核心論據得到了絕對的認可。
美國哈佛大學戴維斯歐亞研究中心前主任、著名的葉利欽問題研究專家柯爾頓(T. Colton)教授曾指出,按照1993年憲法第135條規定,憲法最核心的第1、2、9章的條款可以被修正的前提是成立“憲法大會”、三分之二多數贊同或訴諸全民公決。但俄羅斯法律上關于憲法大會的構成和任務卻沒做任何規定。憲法第136條規定了議會有權以有效多數票(國家杜馬的2/3和聯邦委員會的3/4)通過一項聯邦憲政法案,提議對憲法第3章到第9章進行修改。但除了必須總統簽署該法案,還需要俄羅斯近100個選區的2/3票的批準方能生效。這樣一來,上述兩項憲法條款所賦予的可修正空間更多是虛擬情境而非現實。
葉利欽煞費苦心設計的高度復雜的憲法修正模式,確保了在整個90年代的混亂時期賦予其合法權力來源的國家根本大法不受撼動,從而在事實上確保了俄羅斯總統的絕對權力和強勢地位。即便是俄聯邦共產黨一度成為國家杜馬(議會下院)第一大黨,但在1993年憲法的框架內,在葉利欽的支持率每況愈下的情況下也未能成功彈劾這位俄羅斯首任總統。葉利欽時代俄羅斯轉型政治中內生的分裂和極化狀態,導致反對派無從挑戰以超級總統制為內核的俄羅斯政治制度。直到2008年,93憲法連一個標點都沒有被改動過,而其設計者葉利欽此時已經告別俄羅斯政壇整整9年。
和葉利欽類似,普京同樣選擇了強人政治的發展路徑,雖然其話語和葉利欽已經形成了較大的區別。普京在某種程度上是極為幸運的,這不僅在于他獲得了葉利欽在關鍵時刻的信任和提拔,還在于整個90年代葉利欽給俄羅斯帶來的災難性后果讓他可以輕易地建立起屬于他的強人政治的根基。在即將接過葉利欽的班、出任代總統的前夕,普京在俄羅斯《獨立報》發表了后來被普遍視為其執政思想核心的要文《千年之交的俄羅斯》,其主要思想可以概括如下:俄羅斯注定是一個偉大的國家,任何二流、三流國家的地位對俄羅斯而言都是屈辱;而強大的國家必然需要強有力的領導人來掌舵,否則就有可能陷入發展困境。
普京在論及國家作用時反復強調:
“俄羅斯即使會成為美國或英國的翻版,也不會馬上做到這一點,在那兩個國家里自由主義價值觀有著深刻的歷史傳統。而在我國,國家及其體制和機構在人民生活中一向起著極為重要的作用。有著強大權力的國家對于俄羅斯人來說不是什么不正常的事,不是一件要去反對的事,恰恰相反,它是秩序的源頭和保障,是任何變革的倡導者和主要推動力。”
這樣一來,葉利欽所倡導的、被當時民意普遍支持的、基于強人政治考量的超級總統制,最終在始于2000年并至少延伸至2024年的“長普京時代”獲得真正意義上的生命力。
2000-2012:普京式強人政治如何成為可能?
在西方傳統政治理論看來,普京這種政治強人的長期執政很不科學。正常的規律似乎應該是:如果當權者可以持續給民眾提供良好福利,民眾在其治下生活得足夠幸福,進而對未來有更好、更高預期的話,選民的投票會傾向于現政權。西方的精英和媒體的主流意見幾乎把普京的強人政治視為俄羅斯的萬惡之源,也因此對俄羅斯總統大選的有效性經常充滿質疑。但嚴格意義上來說,普京參加的2000年、2004年、2012年三次總統選舉的過程恰恰符合傳統選舉政治中的經典假設,即社會經濟形勢越好,老百姓對政治家越信任,獲得勝選的可能性越高;反之亦然。
2000年總統大選,普京是以“救世主”的身份出現的。與垂垂老矣、后期更多是病夫治國的葉利欽相比,普京代表了陽光、健康和希望。整個90年代,俄羅斯經濟情況都很糟糕,轉型之痛讓民眾深感忍受之苦。普京的橫空出世剛好趕上比較好的時間節點。1998年金融危機之后,俄羅斯經濟觸底反彈,由于盧布大幅貶值,俄羅斯產品的國際競爭力反而上升了,再加上油價漸漸走高的有利的國際行情,增長變得不再是夢想。而第二次車臣戰爭又把普京推向了民族英雄的高度。所以,2000年普京首次參選拿到了68%和52.9%的投票率和得票率,無疑符合傳統的選舉政治邏輯。
到了2004年,俄羅斯經濟形勢越來越好,社會安定,90年代的混亂噩夢為有序發展的現實所替代。這一時間段也是普京執政18年來經濟形勢最好的時期,發展速度最快的時期,以及老百姓的期望值最高的時期。當時每年年初俄羅斯民意調查機構都有一個民意調查,詢問受訪者的未來預期。絕大多數俄羅斯民眾那時候都感覺良好,認為自己下一年的可支配收入會進一步增加。基于這一預期,俄羅斯老百姓開始擴大消費甚至提前消費,這又變成了新的經濟增長源。就這樣,普京的政治威望開始鞏固、提升、再鞏固、再提升,成為民眾心目中俄國歷史上最成功的領導人之一。2004年俄適齡選民的投票率和普京贏得總統的得票率分別為64.39%和71.31%,這充分證明了普京“經濟發展換政治支持”這一權力公式的有效性。
2008年,普京避而不用獨聯體其他國家領導人常見的、遭到西方詬病的通過修改憲法來長期執政模式,而是推舉時任總理的梅德韋杰夫上臺做總統,自己轉任總理。這一手“王車易位”的方式在形式上突破了俄羅斯政治傳統,但也從另外一個側面證明了普京在俄羅斯政治中的絕對權威。在1993年憲法框架內,總統相對于其它權力機構無可挑戰的絕對多數權力決定了總理的重要性不高。所以,蘇聯解體后葉利欽和普京選任的總理幾乎都是技術官僚,是克林姆林宮戰略和政策的執行者。
在這一意義上,梅德韋杰夫并不例外。盡管他不是一個政治新人,但其即便不是完全沒有獨立性,其權力也是較為有限的。按照俄羅斯的民意調查,在民眾信任的政治機制中,總理的信任度通常很低。但即便如此,普京一支持,梅德韋杰夫就順利當選,甚至得票率也超過了70%。換言之,普京是將民眾對自己的政治信任兌換成了梅德韋杰夫70.28%的得票率。
2012年,普京再度出山,第三次競選總統大位。俄羅斯憲法確實規定總統只能連任兩屆,但也沒有明確規定禁止間隔一段時間后再次參選并當選。在一定程度上,普京利用了俄羅斯根本大法上的一個瑕疵,并引起了西方的強烈批評,外部壓力不小。關鍵的問題還在于,2008年以后俄羅斯經濟形勢急轉直下。當歐美經受次貸危機和金融危機的風暴沖擊時,普京曾認為俄羅斯是風暴中平靜的港灣。但他沒想到話音落下不久,俄羅斯就卷入了風暴,且從此經濟發展乏力,甚至在2014年烏克蘭危機爆發前就被經濟學家批評有增長無發展。所以,2012年那次總統選舉,一方面,普京只要參選就能當選是沒有疑問的,西方即便對俄羅斯的民主充滿了偏見和質疑,在這個問題上也早就有了和普京團隊一樣的結論。但另外一方面,能否贏得更體面對克里姆林宮具有重要的戰略與價值,西方的批評和質疑恰恰是在這個層面上。
根據俄羅斯官方統計,2012年俄總統大選的投票率和普京的得票率分別為?65.34%和63.60%,不能算不高,但和2004年和2008年相比頗有不如。而西方則傾向于認為這些數據都有一定的水分,并提出了兩個方面的質疑:
第一,部分地區的數據過于異常。84個聯邦主體中,至少有5個地區的數據在西方看來存在問題。車臣近100%的支持率,怎么看怎么不科學。畢竟這是一個曾經造過反、鬧個獨立,且至今事實上更是獨立王國的聯邦主體。在西方看來,車臣等地如此心向普京本身就是最大的疑問。凡是普京得票率在90%-95%的地區,按照西方的選舉政治邏輯都應是被質疑和挑戰的對象。
第二,普京疑似動用了手段做票。當然,這不是說完全造假,但西方很多分析家堅持認為克里姆林宮用了很多行政手段作為杠桿來塑造選民投票傾向及行為。其中,他們認為最值得關注的是民意調查的政治化運用。抽樣調查有一套方法,西方主要質疑的是像全俄羅斯輿情研究中心這些親政府的民意調查機構的數據在多大程度上是真實可信的,而獨立調查機構發展環境的變化似乎也給了這種懷疑論者口實。西方研究者懷疑,俄羅斯親克里姆林宮的民意調查機構經過后蘇聯時期的長期運作,已經掌握了選舉控制的政治技術,熟稔何時、何地釋放何種民意數據,以引導民意、引導投票行為。根據西方學者的評估,可能普京的實際得票率接近但不到50%,按規定不過半數就要進行第二輪選舉;而只要進行第二輪,對普京來說就會是失敗,哪怕第二輪普京照樣能拿下。
無論這一說法的可信度如何,我們無法否認的是,2012年俄羅斯總統選舉中的投票率和得票率與普京四年總理任內的經濟形勢有相當的正相關性。2008年之后的俄羅斯經濟增長放緩,部分消解了此前八年普京積累的人氣、威望,也導致了2012年相比于2008年他力推梅德韋杰夫做總統時選情下降的現實。以上是普京執政18年的政治-經濟邏輯。
2018-2024:俄羅斯強人政治的新周期
克里姆林宮對2018年總統大選的重要性有清醒認識,選前也曾經做了一個雙70%的預案,即投票率和得票率都要爭取超過70%。因為這是普京第四次沖擊總統寶座,如果把他從2008年到2012年名義上擔任總理但實際上仍是俄羅斯權力最高統治者的時間也算上,加上這一次顯然也會順利當選,那么普京將執掌俄羅斯權力體制長達24年。未來6年,普京必須要有足夠的合法性、正當性,所以克里姆林宮的政治技術專家們就設定了上述兩個70%的目標。這也是汲取了2016年俄國家杜馬(議會下院)選舉的教訓。那一次杜馬選舉的投票率只有47.8%,首都莫斯科只有區區35%。俄羅斯社會似乎出現了一個“沉默的多數”,這也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作為普京執政支柱之一的“統一俄羅斯黨”這一權力黨的正當性。在體制內反對派和體制外反對派對克里姆林宮全力支持的“統一俄羅斯黨”不構成任何實質性挑戰的情況下,選民的審美疲勞導致了上述尷尬結果。對于克里姆林宮而言,如果本次總統大選重復2016年國家杜馬選舉的狀況,那結果將是災難性的。
與普京前三次總統競選不同,俄羅斯當下整體的發展情況不容樂觀,這對實現雙70%的目標極其不利。2014年烏克蘭危機之后,在西方制裁、油氣等國際大宗商品價格下行和本身經濟的結構性弊端這三重因素的同時作用下,俄羅斯經濟進入了前所未有的低迷期。最近幾年來,只有2017年俄羅斯經濟實現了正增長,以至于普京在當年年底的記者招待會上不等提問就幾次迫不及待地想主動談經濟向好的態勢。實際上,俄羅斯經濟去年一年增長率不足2%,和世界主要經濟大國和新興經濟體相比沒有任何速度和規模優勢。受這樣的增速以及整體受制裁等因素拖累,俄羅斯人的生活水準近幾年不斷下降。
問題在于,以往幾次總統選舉都有一個經濟發展態勢和政治支持程度的正相關性,而這一次民眾的基本預期是接下來6年內俄羅斯將面臨比2012年更為復雜的國內國際環境,經濟上要打高增長翻身仗的可能性同樣比較低。那么,為什么普京在2018年的總統大選中獲得如此高的得票率?為什么俄羅斯選民不管經濟社會形勢如何變幻依然對普京這么不離不棄,生死相依?
其實,關鍵的節點就是2014年烏克蘭危機。這場至今仍看不到解決希望的地緣政治危機,其在內政層面上最重要的功能就是,普京借此最終生成了他作為一個全能型領導人的無可爭議的角色和地位。以前普京及其團隊需要去有意識地構建、營造這樣的形象,全世界經常看到普京隔一段時間就有“可上九天攬月,可下五洋捉鱉”式的秀肌肉、秀才藝的種種場景?。這本身就是強人政治不可或缺的形象構建部分,彼時彼刻的普京也需要這樣的偶像崇拜,以獲得更多、更持久的執政資源。
但烏克蘭危機之后,這種需求變得不再那么重要。2018年總統大選,普京一如既往地不屑和其他的候選人進行同臺電視辯論。最鮮明的對比是,普京這次居然沒有任何正式的競選綱領。2012年他好歹還在報紙上發表7篇長文,專門來宣講自己在政治、經濟、社會、外交等問題上的基本立場和理念。這一次,這種常規動作都沒有了。2017年底的記者招待會和推遲了幾個月才在2018年3月1日舉行的國情咨文發表,變相地成了普京闡述自己政綱的平臺。但和以往相比,這一次普京對于未來執政愿景的表達似乎不夠系統,也少有新鮮話語。相反,倒是躋身世界經濟五強這樣的發展目標被再次當作核心指數推出,其實,這一目標在2007年即被提出,2012年已經被使用過,且按當前發展態勢幾無可能實現。
普京今年以創紀錄的高票贏得第四次總統大選的勝利,克里米亞效應體現得淋漓盡致。此前18年內以經濟發展換取政治支持的普京權力公式開始被經濟和政治分離的規則替代。在某種程度上,普京已經完成了執政正當性來源的轉換,收回克里米亞使嵌入俄羅斯政治傳統的領袖評估和認知模式重新發揮作用,使得他可以無需過多倚賴經濟因素。
俄羅斯評價政治強人成功得失的傳統標準對這一政經分離現象提供了合理解釋。作為軍事強國,俄羅斯重視領土問題,這是衡量領導人執政水平諸多影響因子中最關鍵的一個。蘇聯解體后,俄羅斯多次針對歷史上本國領導人的評價方面展開調查;從調查結果看,凡是曾經有過開疆拓土之功的俄國領導人排名都比較高,凡是導致俄羅斯大國地位受損的領導人獲得的認可都比較低。彼得大帝、葉卡捷琳娜大帝、斯大林以及當下的普京是前者的標志性人物,列寧、戈爾巴喬夫、葉利欽等則歸于后者序列。
普京對俄羅斯民眾這種結構化的經典認知顯然了如指掌,并且充分利用由此衍生的政治文化傳統為自己的正當性提供養分。一份有意推遲、為大選服務的國情咨文,其總長近兩個小時,普京花了42分鐘大談特談俄羅斯在軍事領域的各種殺手锏,但只花了12分鐘左右的時間直接來講經濟和工業。從時間分配可以看出,普京想要傳遞給民眾的首先是一個擁有殺手锏的大國形象,這一遵循俄羅斯傳統政治邏輯的話語對俄羅斯人有極強的感染力。對他們來講,國家的強盛比個人的日子過得好不好更重要。基于同樣的理由,普京近年來在接受國內外的訪談中,經常強調2008年8月8日俄羅斯和格魯吉亞的“五日戰爭”以及2014年的烏克蘭危機后的克里米亞“回歸”的決策,是他一個人做的。普京清醒地認識到,這些關乎國運的重大關鍵節點是塑造他長期執政的正當性的關鍵所在,可以提供遠高于經濟發展的政績支撐。
所以,2014年烏克蘭危機之后,在把克里米亞“收回”俄羅斯版圖的那一刻起,普京就自動獲得了一個可以與斯大林、彼得大帝這樣一些在歷史上被稱為“大帝式”的人物共同的、甚至有過之的神話式正當性。這毫無疑問是2018俄總統大選普京的最大的支持來源。
強人政治的老問題能否解決?
普京在2018年總統大選中無可爭議地勝出,意味著俄羅斯政治進入了“長普京時代”的新周期,但困擾俄羅斯發展的那些老問題依舊存在。
第一,俄羅斯政權交替的問題如何解決。2008年,梅德韋杰夫代表普京取得總統大位后,即推動了普京一直避免的憲法修正,將下一次開始的總統任期從4年改為6年,相當于為普京長期執政提供了一個憲法支撐。2024年,普京的第二個連選連任的總統任期即將結束。屆時72歲的普京似乎很難重啟“王車易位”程序,和梅德韋杰夫再次互換角色,然后在78歲時開始第三個連選連任的總統長周期,直至90歲徹底退出俄羅斯政壇。
換言之,當普京在2024年結束本輪總統任期時,俄羅斯政治權力的延續或斷裂將成為克里姆林宮一個不容回避的問題。如果整個俄羅斯執政精英團隊要求普京繼續掌舵,那么,修改總統最多連任兩次的憲法規定恐怕在所難免。另外一種可能的情境是,普京當局將不得不效仿此前很多獨聯體國家領導人通過全民公決延長總統任期的做法,盡管克里姆林宮迄今為止都不想使用這種注定會引起西方強烈批評的手段。當然,順理成章地直接退出俄羅斯政壇,或者形式上退出、繼續事實上掌控或部分掌控也是一種可以接受的方式。但無論如何,“2024問題”或將持續存在于普京4.0的整個周期,俄羅斯走向何方這個歷史性命題仍將存續并表現出新的時代特征。
第二,在“2024問題”貫穿整個新周期的情況下,如何確保普京體制的穩定性。近年來,克里姆林宮開始啟動精英更替的政治工程,一部分曾經在普京團隊中發揮過關鍵作用的“老近衛軍”慢慢淡出政治舞臺,“新近衛軍”接班上崗的態勢已經形成。新團隊中部分人屬于政治新人,但更多的還是在克里姆林宮序列中慢慢成長起來的成熟技術官僚,以及一部分子承父業的二代精英。新舊精英的漸進式轉換同樣意味著尋租利益集團的局部調整,也必然帶來一定范圍內的利益重組。由于權力-產權共占同構的傳統政商關系結構在普京時代同樣發揮著作用,普京的親信和朋友在不同戰略產業內都擁有足夠的話語和實際權力。被評論界稱為普京政治局2.0版及與之匹配的更大范圍內的政治-經濟精英組合的更新升級,必然帶來安撫舊精英和穩住新精英的雙重任務。
對于克里姆林宮而言,盡可能地減少新舊轉換可能帶來的局部動蕩,重新分配內部的資源和紅利,以及最大限度地創造獲勝集合,自然而然地變成了最大的政治。換言之,普京在未來6年執政能否做到穩穩當當,與能否用較低成本維持整個執政團隊的內部團結有密切關聯性。因此,做大側近人士及更廣泛意義上的分利集團的紅利蛋糕,為各路精英提供新的分利機制,使普京體制的穩定性得以加強,成為了必然選項。
第三,俄羅斯經濟如何走出有(低)增長無發展的困境。2017年,俄羅斯經濟雖然逐漸擺脫了國際大宗商品行情持續走低、西方主導的精確制裁壓力增高的負面影響,終于走出“零/負增長陷阱”,但這并不意味著俄羅斯從此告別了被部分經濟學家批評為“有增長無發展”的舊模式。歷史遺留的過于依賴石油、天然氣等資源類商品且不斷固化的“俄羅斯病”遠未解決,本輪GDP增長似乎仍然是國際油價回暖的產物,而并非經濟結構調整到位的結果。自烏克蘭危機以來,俄羅斯被迫實施進口替代戰略并獲得了部分的成功,但其在很多領域進展并不如意。為了應對可以預見的養老金等福利基金的巨大空缺,克里姆林宮不得不依托在議會的優勢權力結構,強行通過延長退休年齡的相關法案,這對俄羅斯經濟的長期影響尚需觀察。更關鍵的是,新一輪技術革命中俄羅斯的比較優勢正在不斷削弱,傳統的支撐GDP增長的國防訂貨,其作用隨著軍事預算總量的下調,可能將不再特別明顯。總的趨勢是,俄羅斯經濟在短期內幾無可能重歸普京頭兩個總統任期內的高速增長,低速增長的大趨勢很難修正。
普京可以打破經濟發展換取政治支持的經典邏輯,贏得2018年總統大選,但這絕不意味著經濟發展在新政治周期內失去了意義。毫無疑問,如果能推動俄羅斯經濟在未來6年內重返強勁或可持續增長的軌道,勢將需要更扎實的民眾滿意度和支持度,這對普京妥善解決“2024問題”都將有極大裨益。俄羅斯部分精英近期開始用購買力平價來計量俄羅斯GDP在全球的排名,這似乎表明,克里姆林宮對使用實際匯率計價的GDP沖進世界五強已不抱希望,這在事實上表明經濟問題的政治性在普京新的強人政治周期內依然具有重要的指標意義。
第四,如何處理好與西方世界的關系,構建一個有利于自身發展的國際和地區環境。烏克蘭危機結構性地改變了俄羅斯與西方的關系,也使得自冷戰結束以來經歷過多次周期循環并經常下降的國家間關系屢創新低。普京曾經的助理、也被公認是普京意識形態領域的操盤手——蘇爾科夫前一段時間甚至發出俄羅斯注定百年孤獨的感慨。迄今為止,盡管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現出強烈的改善對俄關系的愿望,但美俄兩國國內彼此促進的反俄/反美與排俄/排美的思潮及政治力量,依然在強烈地影響和塑造著兩國關系議程。俄美關系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正常化并獲得足夠的發展動力,仍有較多的不確定因素。而自視為規范性權力的歐盟,受制于內部高度復雜的決策模式,其對俄政策仍建立在戰略疑慮的基礎之上,在烏克蘭危機沒有獲得足夠的緩解前,全面松綁歐俄關系的可能性不大。
問題的悖論在于,對于大國地位的追求已經被鐫刻到俄羅斯的民族基因上。普京在葉利欽轉交總統權力的前一天于《獨立報》發表的長文就警示俄羅斯幾個世紀以來首次有淪為二流甚至三流國家的風險。俄羅斯學術界和決策圈都認為俄羅斯與西方關系持續惡化的根源在于,俄羅斯沒有被西方視為平等伙伴而更多被當作小跟班、依附者,以及由此所帶來的民族屈辱感。俄羅斯的戰略關切是否可以隨著西方更多將競爭焦點轉向中國而獲得部分滿足,至少在普京強人政治的新周期內仍具有較多的不確定性。
小結
整體而言,廣袤無垠的空間及附屬于其上的豐厚資源儲藏,既是世界上其他國家羨慕、嫉妒但又無法恨的俄羅斯的比較優勢,又是俄羅斯快樂并痛著,且難以跳脫地影響其發展路徑的比較劣勢的根源所在。俄羅斯政治強人和強人政治賴以生存的土壤和發展空間都植根于此。普京以絕對的優勢和不同于前三次總統大選獲勝的邏輯贏得了2018年總統大選,標志著俄羅斯在其治下的強人政治新周期。馬基雅維利在其《君主論》一書中曾指出,領導者對事件發展的影響不僅取決于其本人的主觀才能,而且受命運所給予他們的難以測度的偶然因素以及客觀機遇的制約。對普京及其執政團隊而言,這似乎意味著,如果不能妥善解決好影響俄羅斯長期發展的一些老問題,俄羅斯政治的穩定性、發展的可持續性以及國際身份認同中的東西方悖論等經典問題,在2024年后說不定會以較為劇烈的方式表現出來。
(作者單位: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