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羅志田 ? 四川大學(xué)歷史系
明年是五四運動一百周年,媒體多未雨綢繆,為此圈文圈人。差不多每十天半月,就會收到不同機構(gòu)和刊物關(guān)于五四周年紀(jì)念的邀約。與一百年相比,十年或是很短的時間了。然而《文化縱橫》十歲了。我們看著它誕生和成長,也感覺時光匆匆如流水,不舍晝夜。
在紀(jì)念五四運動十周年時,梁啟超曾對“天真爛漫的青年們”說:“青年們啊:你要干政治,請你別要從現(xiàn)狀政治下討生活,請你別要和現(xiàn)在的軍閥黨閥結(jié)緣。你有志氣,有魄力,便自己造出十年后的政治土臺,在自己土臺上活動。”
梁先生的話有特別的針對性,因為那時學(xué)生界里“已經(jīng)有許多吃政治飯當(dāng)小政客的人”了。但他所期望的自己造出土臺,在這自己造的土臺上活動,卻曾是五四前后許多青年熟悉的路(不限于政治)。當(dāng)年他們借著白話文的東風(fēng),自己寫文字,自己辦刊物,自己賣刊物,自己買刊物。一句話,他們正是自己造出土臺,給自己創(chuàng)造出了“社會的需要”,并打出了一片天下。
《文化縱橫》的創(chuàng)辦者并非“天真爛漫的青年”,但據(jù)我不充分的了解,在里面具體做事的,基本都是“天真爛漫的青年”一輩。我們常說百年樹木,十年樹人,十年了,《文化縱橫》樹起來了么?答案是肯定的。刊物的成敗或尚不到評判的時候,一群有夢想之人(也常見進進出出)的努力,卻是不能抹殺的。
正如戴震所說,“凡血氣之屬,皆有精爽。其心之精爽,巨細不同。如火光之照物,光小者,其照也近;……光大者,其照也遠”。不論光照的遠近,照物的,便是光。進而言之,蘭克在論證“每個時代都直接與上帝相關(guān)聯(lián)”時曾強調(diào):“每個時代的價值不在于產(chǎn)生了什么,而在于這個時代本身及其存在。”的確,凡是存在的都是有理由的,也自有其道理在。不僅時代,大至文化、族群、國家,小至個人和細事,都有其獨立的“主體性”。刊物亦然。
任何文化,本是歷史地形成的。而一旦形成,其獨特的主體性便落實在歷史之上,更因其特定的歷史發(fā)展而強化。在人類的歷史長河中,十年真如彈指之間,轉(zhuǎn)瞬已過。然而人生如夢,其實沒有幾個十年。
如果看得稍微宏觀一點,十年之前,中國似乎出現(xiàn)了一個從物質(zhì)走向文質(zhì)的轉(zhuǎn)折點——在一百多年的尋求富強之后,至少中國的經(jīng)濟體量已經(jīng)名列世界前茅。相當(dāng)一些人開始感覺到,不論是個體的人生還是國家、民族、社會,還有很多富強不能解決的問題。換言之,富強可以是目標(biāo),卻不必是最終目標(biāo);更重要的是,富強之后,還要有能適應(yīng)富強的人。這方面的培養(yǎng),就是古人說的“富而后教”(中國古代的教和學(xué),都更強調(diào)求學(xué)一方的主動性,故這里的“教”,也可以是自我的培養(yǎng))。
文化從來包括物質(zhì),但文化也向有非物質(zhì)的一面。中國古人既承認衣食足而知榮辱,又強調(diào)“讀書”方式可能改變物質(zhì)對人的支配性影響(即孟子說的“無恒產(chǎn)而有恒心者,惟士為能”)。用今天的話說,就是不忽視物質(zhì)層面的富強,但更重視非物質(zhì)的文化面相。近代出現(xiàn)韋伯(Max Weber)所說的“命運急轉(zhuǎn)”,以富強為國家目標(biāo),導(dǎo)致“物質(zhì)的興起”。其最大的副作用,就是所謂“市道”的流行。如楊蔭杭之所見,“昔人以市井為小人,今日以市井為圣人”,結(jié)果是“舉國上下,皆以市道行之”。
簡言之,近代的尋求富強使我們的思維和想象都已相當(dāng)物質(zhì)化。如今中國已接近富強,卻也淡忘了富強之外的天地。我們對各類“非物質(zhì)”的事物久已生疏,甚至把“非物質(zhì)文化”視為招商的選項,是讓非物質(zhì)文化更物質(zhì)化的典型表現(xiàn)。就此看來,從物質(zhì)走向文質(zhì),仿佛是這個時代急需的。
正是在十年前的轉(zhuǎn)折時刻,《文化縱橫》誕生了。其發(fā)刊詞清楚標(biāo)示出刊物的追求——“文化重建”。想要探索的是“在富國強兵之外,我們需要建立一個怎樣的社會?我們究竟要前往怎樣的方向?我們究竟應(yīng)對人類大家庭做出怎樣的貢獻?”而刊物面對的語境,就是財富的快速增長“重塑了社會的各種關(guān)系”——一些人有錢了,而另一些人沒有(或感覺沒有),于是“人生缺乏意義,社會缺乏文化,國民缺乏意識形態(tài),民族缺乏精神”。更重要的是,刊物發(fā)現(xiàn),“面對歷史”,中國人“第一次喪失了精神文化領(lǐng)域的自豪感和優(yōu)越感”。這背后隱伏的,其實更多是在“面對世界”時,經(jīng)濟數(shù)據(jù)已經(jīng)起來的中國,卻體會到在世界上沒有多少“話語權(quán)”。
在這樣的背景下,不少人熱心于提高中國在世界的說話能力。有人強調(diào)“中國可以說不”,有人直接表示了“不高興”,而《文化縱橫》則選擇了“文化重建”。其“面對歷史”和“面對世界”的關(guān)照,體現(xiàn)出立足于此時此地的責(zé)任心。蓋讓人傾聽的前提是發(fā)自內(nèi)心的尊敬,而人必自尊然后他人尊之,人必尊人然后他人尊之。
文化重建不是一件簡單的事。尼采曾提出“重新估定一切價值”的主張,被胡適引用來界定他自己推動的“新思潮的根本意義”。《文化縱橫》2010年6月刊的編輯手記,也表出了類似的愿景——“沒有什么是不可以思考的,也沒有什么是不可以重新估量的。”
而2016年2月號的編輯手記,進一步明確了“《文化縱橫》的追求”,那就是“并不試圖辦成一個派別學(xué)人抱團取暖、同聲相求的同人刊物,而是希望直面這個處于急劇變動的中國和世界,提供思考者以一定距離感來觀察和介入這一時勢流變的寫作平臺”,以“激發(fā)更為多元、復(fù)雜且具有內(nèi)在張力的思想和爭論”。
“距離感”的提出真是睿見。我所在的史學(xué)所涉及的理解,都是時空距離較遠的,總有某種可望而不可及的感覺。而這樣一種距離感或許是必須的,甚至可以說是史家的一個優(yōu)勢。若近在咫尺,便不能賦予眾多的豐富涵義。距離可能導(dǎo)致誤會,甚至想入非非,但也可能產(chǎn)生美感。如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所說,近處聽到的教堂鐘聲可能雜亂無章,而遠處所聞,則變得美妙和諧。
正是距離,給予史家一個更高遠的位置,可以從雜亂中感受到和諧,因而獲取對歷史力量和精神的整體把握。聽覺如此,視覺亦然。要有足夠的距離,才能達到林同濟所說的“平眼”,不僅可以有鳥瞰的優(yōu)勢而能見觀察對象之“全景”(total landscape),更能對其中“各個事物相互的關(guān)系”,給予一個“比較近實的估量”。在一個各方意見多元紛歧的時代,與觀察對象保持一定的距離,更容易看到各個事物組成的統(tǒng)相,并及其關(guān)聯(lián)與互動,方足以產(chǎn)生了解之同情,而臻于心通意會之境。
今天回看十年前的中國社會,仿佛隔世,頗有些“十年一覺揚州夢”的感覺。雖說“江南憶,最憶是揚州”,畢竟“孤帆遠影碧空盡,仍見長江天際流”(擅改一字)。無論前塵如何,或不必頻頻回首;風(fēng)吹人醒,還是要面向未來。尤其在這紙媒的好時光已經(jīng)過去的時代,辦刊物的人也只能抖擻精神,從當(dāng)下做起。
以澄清天下為己任的人,有責(zé)任看到多方面的缺失。然而文化在縱橫中呈現(xiàn)出萬花筒般的繽紛絢爛,也并不都是瑕玷。十年前的一件大事,就是汶川大地震。一方面是十萬生命的瞬間逝去,另一方面幾歲的小朋友也可以去救人,最可見孟子說的人皆有惻隱之心。在一個充斥著物化的人欲,甚至人欲已經(jīng)橫流的時代,還能看到這樣顯露本性的現(xiàn)象,特別給人以鼓勵。人性本善,不會被外在的惡徹底消磨掉。讓人性之善盡量的多留一點,這個世界也許還是會變得更好。
與創(chuàng)辦《文化縱橫》的楊平兄相交已二十多年,知道他在所謂的左中右之間是有自己明確定位的。然而這樣的個人立場并未影響辦刊,上引“《文化縱橫》的追求”不僅明確了并不“抱團取暖”,更以“具有內(nèi)在張力”為努力方向。要知道物理學(xué)中的張力(tension)并不像有些人想象的那樣是一種可以“擴張的力量”,而是意味著矛盾甚或沖突。這樣的追求充分展現(xiàn)了“縱橫”意味中那種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期待和包容,也是我對《文化縱橫》的希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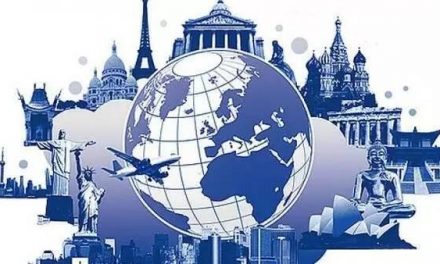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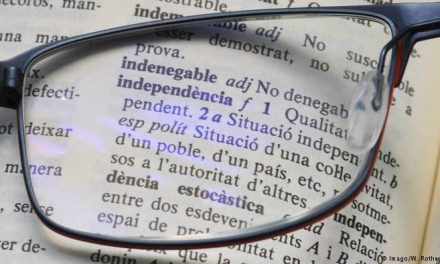








志-150x150.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