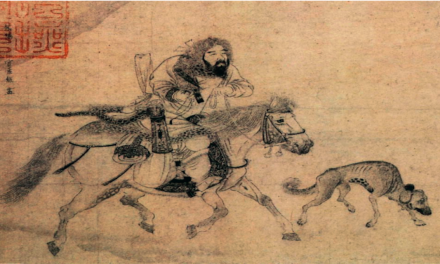[導讀]2015年,田馥甄一首《小幸運》伴隨《我的少女時代》熱映火遍大江南北,“小幸運”或是“小確幸”,從臺灣舶來至大陸,成為當代年輕人口中的流行詞。根據本文作者考證,“小確幸”最早出自于日本作家村上春樹,但并未在日本成為流行語,直至傳到臺灣方遇到適宜盛行的輿論環(huán)境。作者認為,這反映了臺灣大眾心態(tài)的獨特性:在大眾追求“微小但確切的幸福”時,下意識忽略了任何會使身心不愉悅的因素,乃至導致了“對他人的苦難憤懣要不聞,對自身的煩惱困擾也要不問”的普遍現狀。這恰好與經濟疲態(tài)已現、社會貧富差距拉大的臺灣社會相關聯(lián)。民眾通過追求“此時、此地、此我”的幸福,便能以碎片化的感受安慰自我。作者認為,“小確幸”是一種“外貌平和內在戾氣”的消極心態(tài),并由此漠視了大環(huán)境的種種問題。
? 趙剛 | 臺灣東海大學社會學系
“小確幸”這個夾著濃濃東洋風的外來語,來自日本作家村上春樹,說的是生活中“微小但確切的幸福”。臺灣的“時報出版社”分別在2002年和2007年出過的《藍格漢斯島的午后》以及《尋找漩渦貓的方法》這兩本插畫散文集,大概就是這個詞飄洋過海來到臺灣的兩個載體。但這個詞來到臺灣后,浸染流行,成為現在的流行語,大概也不過是這幾年的事。在臺灣,人們對這個詞的掌握大概也無異于村上春樹的本意吧。我問了幾個朋友,有中年人也有青少年,他們的回答,用詞遣字雖有不同,但也不過是多灌下一些水,把原先的三個字泡開罷了。“小小的、確定的、幸福感嘍”──他們說,但這還是難以釋疑。
我會對這個潮名起疑念,想要把它弄清楚,是因為我對它有點直觀的不適,但究竟不適在哪兒,也一時說不清。是因為知識分子放不下的那種精英習氣,總是不甘心隨俗從眾嗎?有可能;我心里頭會冒出這樣的一股質疑的原初欲望,和那個“批判習氣”可能擺脫不了干系。這樣一警惕,于是只要稍加反求諸己并推己及人,也就發(fā)現自己其實不需怎么寬容就能這樣想:有誰不曾在生活或生命的匆忙、壓力、單調、失意或悲傷中,享受過片刻或哪怕是瞬間的安定、喜悅或滿足?
站在一個大醫(yī)院的福利社門口,一個白發(fā)老太太經過你,又轉過身來,很斯文很氣弱地請求你幫她把她手上的剛加過熱的保久乳的瓶蓋給旋開,于是你旋開了,交給她,跟她說:“您慢喝!”,然后你感到一種“小確幸”。或是,一陣帶著童年熟悉氣味的微風突然拂面而過,讓在異鄉(xiāng)的你驚訝感動駐足,直到那氣息與那回憶消失無蹤,于是你有了一段“小確幸”。或是,疲憊不堪的你,跳上一輛公共汽車,找到一個靠窗好座位,慢慢地一站一站地在雨季的夜暮的城市里前進,像一個城市游魂般,你靜靜地安全地端詳著人行道上或行或止的傘下的一張張或怔然或怡然或木然的面龐──于是,“小確幸”吧。
或是,在一個冷冬鉆進一間暖暖的、嘈雜的、燈色昏黃的小咖啡館,吁吁氣、搓搓手,喝上一杯熱咖啡,拿一本平常不會看的雜志,幾乎完全無意識地翻看著,啜飲著──“小確幸”。或是,在一個大夏天午后,走進一家便利店,吃上一個大冰淇淋,比個“V”手勢,來個自拍上傳……這些“小確幸”,如恒河沙數何止千萬,而就算這些不是你或我的“小確幸”,你或我也沒有一點資格質疑別人的“小確幸”。不是嗎?那么,為何“小確幸”這個詞會讓我感到莫名的不安?以下算是我個人的“困而求之”吧。
▍“小確幸”背后的社會隱喻
的確,對待“小確幸”,不能以一種“批判知識分子”的傲慢對之直接否定。但是,是不是可以從而放到另一極端,拒絕將之知識對象化,僅僅看作古今中外無所不在的“小小的確定的幸福感”?我不認為如此。因為這里畢竟牽涉到一個客觀的知識問題:人們?yōu)槭裁丛谝粋€特定的時空中,不約而同地使用了一個新名詞,來指認他們的“幸福感”?
如此說來,“小確幸”應該被視為存在于一種特定歷史與社會條件下的能指,它并非“古已有之”。“小確幸”固然是各個人所經歷的不同的幸福感,幾乎是人言人殊,但如果我們把“小確幸”僅限定于個人層次,那其實也同樣意味著拒絕知識對象化了。因此,有必要將“小確幸”視為一個“社會事件”或“思想事件”,在一個時代的/社會的層次上掌握其“思想意義”。是這個歷史性與社會性的提問意識,允許我從這個名詞的直觀意義中跳出,對其分疏化與脈絡化。
先對它作些概念分疏吧。如其名,它真的必須要“小”,它拒絕和任何大(哪怕是僅僅稍大于自我)的東西掛鉤。因此,“小確幸”和“宗教性”或“類宗教性”(天、道、上帝、良知……)無關。我們當代的“小確幸”與一個歐洲中世紀基督教家庭平日晚餐桌前的晚禱所散發(fā)出的那種“確幸”無關。同樣的,也和古代中國士大夫“無愧平生之志”的那種道德篤定感的“確幸”無關。其次,它經常遠離大自然。不論是“獨坐敬亭山”,或是“悠然見南山”,不管是“華爾騰湖”,或是“茵尼斯弗利島”之類的“確幸”,都與它無關。互聯(lián)網時代的人們既失去了孤獨的能力,也失去了在大自然中感到幸福的能力。再其次,它原則上無須以勞動或任何積極實踐為前提。我們的“小確幸”與東西方農民在稻堆麥垛疇間庭前悠然吸桿兒煙的那種(算是小的)“確幸”吧,也無關,那太折騰了!
但“小確幸”之所以高調唱“小”的最重要的原因,以我看來,是預設了對任何不輕飄的(從而不愉悅的)因素的話語排除;不但對他人的苦難憤懣要不聞,對自身的煩惱困擾也要不問,眼前的固然,歷史中的更是。
說到底,“小確幸”之所以“小”,在于它否定或掩飾時空深度現實,只圖一個“當下”,只爭一個“我的”。古人說“今有滿堂飲酒者,有一人獨索然向隅而泣,則一堂之人皆不樂矣”,近人說“侵略者的炮火使整個華北擺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而這里的“滿堂飲酒”與“平靜的書桌”指涉的既是一種對于“小確幸”的追求,也是追求者同時所深刻自覺的緊張感與不安感,因為自我的小小幸福和超越自我的、更大的、更連續(xù)的歷史與社會之間的連帶是無法斬斷的。
相對而言,我們當今的“小確幸”恰恰是對這些“大”與“深”的切割與隔離,唯其“小”、唯其“扁”、唯其“平”,才能保證其“確”。“小確幸”敘事所預設的社會空間,可能就恰好符合撒切爾新自由主義的規(guī)定:“沒有社會,只有眾個人”。而“小確幸”敘事所預設的歷史時間,則是斷裂的、破碎的、當下的。“此時、此地、此我”是“小確幸”敘事的三個主要梁柱。“小確幸”是一種激進的“社會學想象力”的反命題。
因此,“小確幸”是一個“扁平現代性”的觀念產物,而同時,也反過來支撐這個扁平現代性。“小確幸”是建立在一種高度的世俗性、個體性與民粹性之上,并以商品物質性為其背景。它與任何“崇高”、“偉大”、“道德”、“理想”、“歷史”、“群性”或是“類存在”都無關。是的,就只是“無關”,它連嘲笑它們都懶得,何況批判?
因此,“小確幸”所反映的首先是一種特定的主體狀態(tài)。原子化的主體頻繁地在“發(fā)現”、“發(fā)明”,以及“命名”它的某種其實很容易就流淌過的某種細小的碎片化的感覺,這當然和網絡時代的出現有關,人們表達、記錄、傳播自己的經驗感受的機會比以往不知多多少倍。好比,以前吃過一頓好早餐,也就吃過了,但今天我們可以將這個早餐類宗教儀式地對象化,拍照上傳,和別人分享我們的“小確幸”。“小確幸”常常是一種對“自我”的微笑自拍,是一種對“自我”所比的一種“V”手勢,是一種自我“治愈”。
“小確幸”的被指認與被需求,因此反而泄露了這個指認與需求主體的某種貧困與無奈。當我們把這樣的主體擺放到社會與歷史層次時,我們就更容易理解到“小確幸”是一個在各方面都展現了深刻不確定性的年代中的一個精神現象。仔細檢視一些“小確幸”敘述,幾乎都可察覺到隱藏在它們背后的不被言說的當代家庭(或“親密關系”)、工作(或“勞動過程”)乃至道德審美領域中的某種深刻病理性。這個不被言說的后臺以及拼命被言說的“小確幸”前臺之間的反差,不妨讓我們如此指出:“小確幸”反映的是一種“苦中作樂”,不,其實是“苦中指樂”。
這樣說好了,不必提什么理想國,我們比較難以想象,假使在一個有很多“大”的或“體制化”的人生保障(“確幸”?)的社會里(好比美式福特主義或日式家父長公司或西歐福利國家),或哪怕僅僅是資本主義上升期的社會里,會出現“小確幸”這樣的一種大眾話語嗎?相對而言,當資本主義發(fā)展步向沉滯低迷,當實際工資減少、社會保障被縮遭砍,生產彈性化、超時加班、失業(yè)危機,墜落底層而無安全網時,“小確幸”就成為了一種深具無奈感的個人/大眾需求。它是這個資本主義世界中飽受不確定與無望感的青年人與中年人的挫折與痛苦的一種表達。它是一種失去理想、夢想、未來,或任何自我超越可能的“主體”的自衛(wèi)/自慰性精神狀態(tài)。
于是,在商品時空中散放出來的“小確幸”,事實上透著一股資本主義發(fā)展沉滯期的霉味。難怪這個詞是從經濟長期停滯的日本冒出來傳過來的。你能想象在資本主義上升期中的社會里,會發(fā)展出“小確幸”這樣的流行話語與流行感受嗎?那里有的是資本家及其信徒的狂熱,以及幾乎具有同樣熱力但又有對抗的價值與希望的工人運動。我們都知道資本主義不好,但更壞的是不景氣時代的資本主義。
“小確幸”恰恰就是建立在沒落或沉滯資本主義社會之上,但它不但不提供任何質疑或是反抗這個大環(huán)境的立足點,反而是一種軟綿綿的取消,像是一種沒有熱量的“代糖”,一種掩蓋無力感的“有效感”,一種“每一個人的宗教”,一種不斷自我強制提醒的“幸福”。因此“小確幸”反而倒過來支撐了這個深具問題的體制。在這個意義上,“小確幸”是甜絲絲的的軟化劑,使硬梆梆的支配性政治概念(例如,新自由主義、攫取性個人主義、多元主義、旁觀者政治,以及消費主義)結合成一個巨大的霸權叢結。
臺灣街頭以“小確幸”命名的小吃店
“小確幸” 還蘊含了危機感,例如“小確幸”的“擁有”(“這是我的!”),讓擁有者焦慮──若是哪天連這個也都沒了,那該如何是好?這樣一種對可能威脅的恐懼,對可能敵人的焦慮鎖定,于是就成為了甜絲絲的“小確幸”的同體反面。歷史上的納粹也是一個明顯的例子,他們所追求的即是一種當時德國版的“小確幸”,要在充滿危機的、不確定性的世界中,穩(wěn)固地保有他們謂之“家園”(heimat)的“小確幸”。于是“猶太人”成為了他們的甜甜小確幸的苦苦大前提。
這么說來,“小確幸”遠遠不是日常的、常識的“小小的確定的幸福感”而已,而是資本主義發(fā)展沉滯期所產生的特定文化想象,是精神焦慮不安、物質前景黯淡的原子化個人企圖在當下的感受中以碎片化的經驗安慰碎片化的自我的一種小詭計──這可以說是“小確幸”的一般性考察。
但是,問題來了,有一個好朋友告訴我,其實這個詞在它的發(fā)源地日本,并不曾成為流行語。我問了一個日本通朋友,她說,對耶,我每天都看日文網絡新聞,沒看過這個詞呀。她幫我問了兩個人,一個是大陸人待了日本12年,一個是日本人,這兩位也都異口同聲確定地說“沒聽過這個詞”或“至今沒有在電視里看到或聽周圍日本人用過”。我自己又直接問了一個日本朋友,他說他也沒聽過,他順便評論了一下,說這樣的一種名詞是村上春樹那一代的60年代日本左派后來走上虛無主義的不令人驚訝的普遍狀況。
“沒有小確幸的人生,不過是干巴巴的沙漠罷了”
于是,這個非常有趣的對照就自動提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探索指引:要理解“小確幸”在臺灣的流行,除了得在新自由主義現代性,或資本主義沉滯期的文化再現,這兩塊與日本社會的“交集”之中探索,還要在之外尋找。我將要指出,“小確幸”是一個當代臺灣版的認同政治的建構。
▍“小確幸”是臺灣的“文化無意識”
從1960年代到大約1980年代,臺灣這個社會是不會出現“小確幸”之類的話語的。粗泛地說,那個時代好或不好,都浸潤在某種“理想主義”大話語中。那時,人們當然也在各個角落里尋求他們的小小的確定的幸福感,但那和今日的“小確幸”在精神內涵、表征方式,或是社會分析上,都是有巨大差異的:不大自戀、沒有霉味,也沒有拜物。借用許信良在《臺灣社會力分析》那本書中所用的語言,那時的臺灣人(當然指的是中小企業(yè)主)正“拿著007手提箱”昂然地滿世界跑。
從1990年代到2000年代中期的這十多年臺灣人民也還是不會講“小確幸”或任何相近的話語,因為在經濟上,臺灣的繁榮未退,大陸也還未“崛起”,直至2008年,反觀臺灣的經濟疲態(tài)已現、社會貧富差距拉大,“中國崛起”成為一個不可輕易否認的現實。在臺灣,“中國崛起”或被論述為“中國威脅”(或“中國因素”或“你好大,我好怕”)。另一方面也有源于臺灣社會內部的原因,那就是臺灣社會多年來所積攢匯聚的底氣,由于經濟的持續(xù)低迷、兩黨政治的無盡內斗、社會內部的認同分裂……而消耗殆盡。在這些條件下,“小確幸”得到了滋養(yǎng)它的土壤,就算不曾從日本直接移植來這個字詞,本地應該也會造出一個適合表述它的字詞。
“小確幸”是一個在兩岸分斷對立、臺灣的發(fā)展主義走頹、消費文化持續(xù)高漲、兩黨內斗導致的社會方向感的失落,以及親美友日的現代化文明主義等因素輻輳下的“文化無意識”。用大白話說,其主旨就是:“既然發(fā)展玩不過對岸,那咱就不玩了,我們只玩我們能玩的游戲,即‘綠色’路線、‘文明’路線、‘文化經濟’路線”。于是,“家園”、“文明”、“祥和”、“懷舊”、“禮貌”、“包容”、“人情味”等,在某一方面而言頗具“民國風”的“歲月靜好”的心理狀態(tài),成為了臺灣的一種外貌平和內在戾氣的主流文化想象。是在這種由于不知道如何面對“中國”與世界而產生的某種童稚的、賭氣的、撒嬌的,與幾乎是鎖國自閉的心理狀態(tài)下,臺灣有了“小確幸”心態(tài)的出現。
“小確幸“是臺灣建構主體自尊感的必要條件:我們要以我們的“小確幸”來抵抗你們的大、你們的新、你們的發(fā)展、你們的繁榮、你們的核電全球化……我們要以我們九份三峽的舊館斜陽來映襯你深圳上海的樹小墻新,以我們的“舒國治”(臺灣的“小吃教主”)來訕笑你的“大魚大肉”,以我們的“人”──這道“最美麗的風景”──來睥睨你的暴發(fā)戶與煤老板。
再明顯不過的是,如果臺灣不面對與中國大陸的關系,不面對與全球資本主義的關系,只求“超前地”、“后現代地”、“愿望地”、“美學化地”解決臺灣的“發(fā)展問題”,那么其實就也只是一種“去政治化的政治”而已,而之所以仍是“政治”,則是因為任何牽涉到青年就業(yè)、貧富差距、合理房價、自我實現的“合理發(fā)展戰(zhàn)略機遇”,都將因“小確幸”的無意識而被強迫放棄;對中國大陸的敵對,會因傲慢的“小確幸”而重新武裝;對美日的地緣政治依賴,也會因自卑的“小確幸”而持續(xù)。在一個根本意義上,正因為“小確幸”從來不是問題的提出,所以從來也談不上問題的解決,而只是問題傷疤的濃妝艷抹。
因此,“小確幸”遠遠不只是一個軟綿綿的生活態(tài)度,而能反應其社會心態(tài)。“小確幸”借由“小小的確定的幸福感”這樣的無害的乃至外型甜美的外殼,防止社會苦難向經驗、理論,與社會探索開放。拒絕經驗、歷史與理論介入的后果,就是只有大量依賴隱喻與情緒,這于是形成了臺灣當代主流與知識界的基本狀況。這個狀況何以致之?如何破解?也許是今日臺灣的一個重要問題。
— ?2020年10月新刊目錄??—
▍域外
美歐跨大西洋關系的中國挑戰(zhàn)
任希鵬
▍封面選題:美國的百年未有之變局
01 中美沖突:國際經濟層級體系的裂變
封凱棟
02 尋找新的“敵人” :美國對華戰(zhàn)略加速調整的國內根源
潘亞玲
03 從“帝國”到“國家”:美國國家能力轉型進行時
歐樹軍
04 里根政體的衰敗與美國重建的特朗普道路
左亦魯
05 疫情后大國關系新格局
紀明葵
▍城市政治經濟學
06 全球化時代城市的轉型發(fā)展
周偉林
▍公益理論與公益實踐
07 美國國家構建過程中的科學公益
牛 可
▍技術革命與社會變遷
08 “防疫國家”的信息治理:實踐及其理念
戴 昕
09 區(qū)塊鏈與國家治理的融合重構
李雯佳
▍中國發(fā)展模式再討論
10 進行中的開創(chuàng):華為實踐的工業(yè)史意義
宋 磊
▍社會結構變遷
11 精細分層社會與中產焦慮癥
熊易寒
12 當小農戶邁向大市場
譚同學
▍學術評論
13 文科為什么要交叉——兼論知識發(fā)展的一般規(guī)律
錢乘旦
▍后發(fā)國家發(fā)展道路
14 拉丁美洲的未竟工業(yè)化
程文君 鄭 宇
15 “弱國家”困境和埃及的再工業(yè)化前景
段九州
本文原載于《文化縱橫》2014年12月號。版權所有,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回復此微信獲得許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