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方萌
中國的城市化和美國的高科技產(chǎn)業(yè)發(fā)展將是深刻影響21世紀(jì)人類發(fā)展的兩大關(guān)鍵因素。……中國的城市化將是區(qū)域經(jīng)濟增長的驅(qū)動力,并產(chǎn)生最重要的經(jīng)濟收益。
——諾貝爾經(jīng)濟學(xué)獎得主斯蒂格利茨
13億人的現(xiàn)代化和近10億人的城鎮(zhèn)化,在人類歷史上是沒有的,中國這條路走好了,不僅造福中國人民,對世界也是貢獻。
——中國新任國家總理李克強
戶口制度的“國際化”
羅伯茨(Kenneth D. Roberts)是美國西南大學(xué)的經(jīng)濟學(xué)教授。他在上世紀(jì)90年代發(fā)現(xiàn),中國的農(nóng)民工進城現(xiàn)象同美國的墨西哥移民潮有頗多相似之處。比如,這兩類移民勞工都從事低技術(shù)的底層工作,都與本地人具有文化隔膜,都不具有當(dāng)?shù)卣缴矸荨纱筮w移運動都體現(xiàn)為農(nóng)村和城市之間的往返活動,都由來源地和遷入地之間的經(jīng)濟落差所驅(qū)動。而最有意味的相同點在于,中國城市和美國政府都在不同程度上限制著這兩股遷移潮流。羅伯茨在他的論文中觀察到:“這些相似之處讓中國的情況看起來不像是國內(nèi)遷移,更像發(fā)展中國家與發(fā)達國家之間的國際遷移。”
冷戰(zhàn)以后,社會主義國家大都采取了嚴(yán)格的居住管理制度,不僅對國民的國際遷移層層設(shè)卡,也對國內(nèi)流動設(shè)置了行政障礙。蘇聯(lián)人在各加盟共和國之間旅行,還須持有一種特別的“內(nèi)部護照”,蘇聯(lián)也被西方諷刺為“護照國家”。這類居住管理體制,結(jié)合承擔(dān)公民福利的單位制度,在相當(dāng)一段時間內(nèi)大大減低了勞動力的跨區(qū)流動率。然而,市場化改革要求統(tǒng)一全國勞工市場,也要求按能力標(biāo)準(zhǔn)對人力資源進行有效配置。作為對要素價格的反映,勞動力必然流向回報率更高的發(fā)達地區(qū)。
盡管沒有做好準(zhǔn)備,轉(zhuǎn)型國家的改革家們不得不面對“半開放社會”促生的遷移大潮。由于蘇聯(lián)的加盟共和國紛紛獨立,內(nèi)部護照也失去了其管理功能,它們之間的人員往來變成了真正的國際移民。而在中國,長期沿襲的戶籍制度以城鄉(xiāng)二元結(jié)構(gòu)為基礎(chǔ),構(gòu)成了國內(nèi)的發(fā)達地區(qū)和不發(fā)達地區(qū)。改革開放后這兩大地區(qū)的邊界管制逐漸松動,農(nóng)村勞動力可以流入城市打工,小城鎮(zhèn)的居民也可以來大都市謀生。然而,中國的發(fā)達地區(qū)像世界上的發(fā)達國家一樣,希望外來勞工群體“召之即來,揮之即去”。城市部門對外來勞工存在需求,卻不承認他們應(yīng)當(dāng)享有市民身份。與此同時,中國的戶籍制度并非沒有松動,各個城市向社會精英敞開了大門。
1990年代,公安部曾兩度下發(fā)文件,允許地方城市根據(jù)當(dāng)?shù)貭顩r對外來人口給予戶籍,地方政府設(shè)立的準(zhǔn)入標(biāo)準(zhǔn)遂成為落戶城市的唯一途徑。中國城市由此獲得了一項“自治權(quán)”,可以自由決定接受或排斥哪些外來人口。就像發(fā)達國家一樣,各市政當(dāng)局主要向三類人開放了戶口遷移渠道:有錢人可以通過買房或設(shè)廠(投資移民),聰明人可以憑靠學(xué)歷或職稱(技術(shù)移民),還有些人可以借助家庭關(guān)系(親屬移民)。
各國移民門檻高低不一,中國城市的落戶標(biāo)準(zhǔn)也寬嚴(yán)有異。一般而言,經(jīng)濟發(fā)達的大城市很嚴(yán)格,而人口稀少的小城鎮(zhèn)較寬松。在首都北京,國外名校的碩士文憑都難以保證落戶京城;在許多三線城市,找到正式工作的國內(nèi)本科生就可以解決當(dāng)?shù)貞艨凇H化的上海在戶籍政策上也最為西化——當(dāng)?shù)卣苯咏栌昧思幽么蟮囊泼穹e分制,根據(jù)一個人的工作單位和個人特點打分加總,達到一定分數(shù)即可獲得上海戶口。了解到中國近年的政策變化,羅伯茨教授也許會感嘆:不僅中國的移民現(xiàn)象近似國際遷移,西方國家的移民政策也為國內(nèi)政府提供了參考依據(jù)。
城市體系與人口控制
筆者的研究興趣之一正是國際人口遷移,因此對發(fā)達國家的移民政策較為熟悉。我留學(xué)回國后接觸了一些戶籍改革的材料,總有似曾相識之感。從框架體系到實施細則,中國的戶籍制度演化得越來越像國際移民體制,只是缺乏一道長長的邊境線。
中國人所屬的社會階層也對應(yīng)著相應(yīng)的遷移權(quán)利,擁有財富、技能或關(guān)系資源的社會精英受到每座城市歡迎,成為實現(xiàn)自由遷移的中國公民;而底層的農(nóng)民工則像發(fā)達國家的非法移民,難以享有城市居民的社會福利。
這種戶籍制度產(chǎn)生了一大批不具有市民身份的城市人口。2011年末,中國總?cè)丝诮?3.5億,城鎮(zhèn)人口約為6.9億,其中包括1.6億不具有城鎮(zhèn)戶籍的外來務(wù)工人員。在戶籍準(zhǔn)入最為嚴(yán)格的北京,這一狀況更為明顯。2011年底,全市常住人口2018.6萬人,其中三分之一強(36.8%)不具有本市戶籍。而在當(dāng)年新增人口中,近三分之二屬于這類外來人口。
不少人認為大城市的承載能力已經(jīng)飽和,無法容納更多移民,應(yīng)當(dāng)強化針對總?cè)丝诤蛻艏丝诘碾p重控制。在發(fā)達國家反移民的聲浪中,這種馬爾薩斯式的論調(diào)也不絕于耳。可實際上,自工業(yè)革命以來,各級城市的規(guī)模一直在擴大,甚至出現(xiàn)了上千萬人口的超大城市。城市擴容具有人口集聚的規(guī)模效應(yīng)和外部性,有利于就業(yè)增長和經(jīng)濟發(fā)展。人們一般認為大城市比中小城市浪費了更多能源,其實就使用效率而言恰恰相反。生物學(xué)家發(fā)現(xiàn),哺乳動物的單位能耗與體重成反比——例如北極熊體形越大,為每磅肉消耗的能量就越小。國外研究也表明,以每萬人擁有的加油站計算,大城市比中小城市建設(shè)的加油站更少。
當(dāng)然,王熙鳳對賈府的評論也有道理——“大有大的難處”。任何試圖擴張的人類組織,從大學(xué)社團到民族國家,達到一定規(guī)模后都會受到發(fā)展約束。這里我們可以拓展英國經(jīng)濟學(xué)家科斯分析企業(yè)邊界的思路:一種組織的擴張成本超過其擴張收益時,它就應(yīng)當(dāng)適可而止了。具體到城市這類空間型態(tài)的組織,它們的發(fā)展可能受到天然屏障或資源供應(yīng)的硬性約束,比如建設(shè)在盆地中的城市很難向周邊山區(qū)擴展,而水資源短缺也構(gòu)成了人口增長的瓶頸。
更重要的是,城市會因自身發(fā)展而停止擴容。隨著一座城市的人口增加,每遷入一位勞工的邊際成本也會上漲,這些成本包括住房價格、日用品開銷和交通擁擠程度等因素。同時,污染和犯罪問題也可能日趨嚴(yán)重。當(dāng)大城市變得越來越不宜居,人們就會考慮遷移到規(guī)模小的二線城市,像近年來大學(xué)畢業(yè)生自發(fā)進行的“逃離北上廣”運動。而二線城市的人口增長,又會引發(fā)某些群體向更小的三線城市遷移。具有充分選擇權(quán)的前提下,自由遷移機制可以通過個體行為靈活調(diào)節(jié)城市規(guī)模。
我們需要討論的關(guān)鍵議題,也就不在于大城市可以容納多少居民,而在于國人是否有權(quán)選擇成為某座城市的市民。中國目前對城市人口,尤其享有各項福利的戶籍人口,實施了相當(dāng)有效的規(guī)模控制。這一控制的前提有二:一是進城務(wù)工人員自愿回歸家鄉(xiāng);二是農(nóng)村能夠承擔(dān)這批流動工人的再生產(chǎn)成本。而對于新生代的移民工人,這兩項前提漸漸都不能得到滿足。許多調(diào)查發(fā)現(xiàn),絕大多數(shù)新生代民工渴望定居城市,農(nóng)村對他們而言是陌生的。隨著中國產(chǎn)業(yè)升級,對工人技能要求也在提高,農(nóng)村的基礎(chǔ)教育并不能提供必要的人力培訓(xùn)。
早在1960年代,美國政治學(xué)家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就發(fā)現(xiàn)了發(fā)展中國家的一個普遍現(xiàn)象:“第一代的貧民區(qū)居民將社會禮讓和政治消極這些傳統(tǒng)的農(nóng)村觀念帶入貧民區(qū),他們的孩子卻是在城市的環(huán)境中長大并接受城市人的目標(biāo)和期望。父母滿足于地理上的橫向移動,孩子則要求在地位上垂直上升。”他由此提醒政治家們:“如果這種機會不能很快到來的話,貧民區(qū)內(nèi)的激進主義就將顯著地增強。”城市移民的市民化不僅屬于經(jīng)濟問題,也是關(guān)乎社會穩(wěn)定的政治問題。
城市化的改革方向
中國正在進行人類歷史上最大規(guī)模的城市化進程,推進城市化的政策議題也成為當(dāng)前政府關(guān)注的焦點之一。目前的居住管理體制造成了大量外來移民的身份模糊狀態(tài)。非戶籍常住人口被習(xí)慣性地稱為“流動人口”,意味著他們不具有穩(wěn)定的合法身份。這種模糊狀態(tài)不能維持一個社會的長治久安,新任國家總理李克強曾在不同場合強調(diào):“把符合條件的農(nóng)民工逐步轉(zhuǎn)為城鎮(zhèn)居民,是推進城鎮(zhèn)化的一項重要任務(wù)。”如何逐步實現(xiàn)新時期的市民化,正是目前戶籍改革的首要問題。
中國的國內(nèi)遷移類似國際遷移,我們也可以借鑒發(fā)達國家針對外來移民的融合政策。在歐美等國,持有永久居留證和臨時工作證件的外籍移民除了不具有投票參選等政治權(quán)利,一般都被要求加入所在國家的社會保險網(wǎng)絡(luò),同時也享受相應(yīng)的醫(yī)療和失業(yè)保障。換言之,他們的經(jīng)濟權(quán)利和社會權(quán)利在居留期間得到了與國民相同的待遇。目前中國一些城市啟動的居住證制度,也試圖將移民群體納入本地的社會保障體系。例如,2011年蘇州市的試行辦法規(guī)定,使用居住證的流動人口可以更加方便地享受各項公共服務(wù)。
盡管居住證制度提升了流動人口的市政服務(wù),他們與戶籍人口的福利差距并不會因此消除。2010年,廣東實行了積分入戶政策,外來務(wù)工人員達到一定積分后,其子女可享受公共教育。番禺全區(qū)共有18萬學(xué)生處于義務(wù)教育階段,將近一半(46.6%)為外來人員子女,而該區(qū)僅有474人在2011年憑居住證加入了“積分入學(xué)”計劃,免費入讀公立學(xué)校。
一個國家的福利水平越高,對合法移民的資格要求也就越嚴(yán)。歐洲雖然面臨比美國更嚴(yán)重的老齡化和人才短缺問題,吸收的外籍移民卻不如美國數(shù)量多,主要原因即在于此。類似地,中國各大城市的戶籍身份也對應(yīng)著一系列社會福利,在這些福利項目未能全國統(tǒng)一和異地轉(zhuǎn)移的情況下,市民待遇較高的大城市缺乏動力為外來人口提供同等的社會服務(wù)。
除了相對的高福利體制,中國發(fā)達地區(qū)還享有一系列特權(quán),當(dāng)?shù)卣硬辉杆蓜討艏拗啤T诘胤秸疇幦≠Y源的行政博弈中,大城市往往占據(jù)更多優(yōu)勢,有能力獲得中央政府的政策傾斜。比如北京上海等地考生更容易被名牌大學(xué)錄取,這也是“異地高考”等問題產(chǎn)生的原因之一。不過,這也提醒我們,中國城市畢竟不同于世界諸國,而受制于一個掌控全局的中央機構(gòu)。
1978年以來的中國改革始于放權(quán)讓利,區(qū)域競爭也積極推動了經(jīng)濟增長和社會發(fā)展。然而,下放權(quán)力并不能完成所有改革,集中權(quán)力對于推行某些政策十分必要,尤其在地方勢力形成強大的利益集團之時。盡管戶籍改革困難重重,決策者還是應(yīng)當(dāng)清楚地看到,地方政府的戶口政策有將中國城市化推向“國際化”的趨勢,這鞏固了社會精英和區(qū)域經(jīng)濟的既得利益,卻使中下層民眾較少享受到城鎮(zhèn)化帶來的改革紅利。
在去除地方特權(quán)化和推動福利國家化的基礎(chǔ)上,中國才有可能縮小各地公共服務(wù)的巨大差距,降低大小城市的準(zhǔn)入門檻,進一步促進全國范圍的自由流動。當(dāng)我們將遷移視為發(fā)展的題中之義,中國將實現(xiàn)一場真正意義的“國內(nèi)移民”。
(作者單位:北京師范大學(xué)社會發(fā)展與公共政策學(xué)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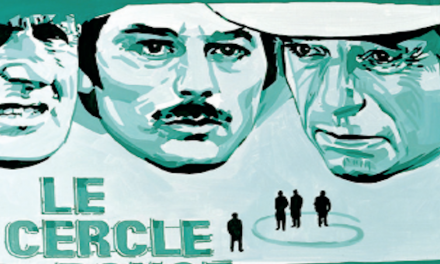







志-150x150.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