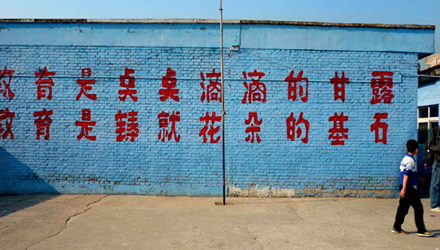? 祝東力
[導讀]今天是法定上班日的最后一天,反復的疫情卻讓今年春節有所不同。以往在社區街道看到“家是最小國,國是千萬家”的宣傳海報,如今有了具體的含義,那就是是否要為國家減輕負擔、相應“就地過年”的號召。若換個角度思考,身處大流動社會,“家”能否跨越傳統觀念的地域屬性,擁有更廣泛的含義?祝東力先生通過考察百年中國對于“家”、“國”觀念的變遷,探索了“家”、“國”位置在國人精神世界的變化。他指出,家庭作為中國傳統社會的基礎價值,曾為中國人提供了一個安身立命的價值基礎,也為家庭、國家的鞏固提供了合理的道德觀念。如今面對急劇的社會轉型,他發問,“未來是從家庭到個人、走向真正的原子化社會,還是有可能回歸社會和國家?” 而這又如何“決定中國的前景”?本文原載《文化縱橫》,僅代表作者觀點,特此編發,供諸君思考。
家,是中國傳統社會的基本單位,既是經濟的基本單位,也是價值觀的基本單位。
經濟是基礎,先說經濟。自戰國以來,無論是自耕農,還是佃農,以一家一戶為單位經營農業,同時兼營家庭手工業,這種類型的小農經濟,就一直是中國傳統經濟的基礎和主體。西漢文帝、景帝時代的晁錯,有段話很有名,他說:
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獲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徭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吊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
(《漢書·食貨志》)
這是對當時小農之家的描述,其實也適用于整個中國傳統社會。這樣的五口之家,勤勞節儉,含辛茹苦,以一兩個主要勞力,加上輔助勞力,憑借最簡單的農具(鋤、鐮或犁),隨時隨地都可以同傳統的生產資料,即土地相結合,進行簡單再生產。經過編戶齊民,這種分散細碎而又數量龐大的小農,便構成了國家賦稅徭役——傳統社會經濟剩余的主體部分——的來源。因此,在中國古代,一端,是數以千萬計的細弱孤立的小農;另一端,是皇權─官僚階級的強大國家機器。“小農經濟”,歷來就是“大國政治”的經濟基礎和社會土壤。
這種家庭經濟,結構簡單而脆弱,面對水旱災害、豪強兼并、苛捐雜稅和社會動亂等,極容易破產。但另一方面,唯其簡單,也極容易再生和復制,有著極其頑強的生命力。中國歷史上,多少舊王朝傾覆,多少新王朝誕生,全都有賴于小農經濟這種辯證的“既脆弱又頑強”的結構。
家庭經濟在社會經濟中的這種基礎作用,決定了“家”在價值譜系中的特殊地位。孔子說:孝敬父母、尊敬兄長,是道德的根本(“孝悌也者,其為仁之本歟。”)。在“三綱”(董仲舒:“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五倫”(孟子:“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等基本的道德準則中,家庭倫理占有最大的比重。這種現象的實質在于,以父子、夫婦、兄弟為架構的家庭秩序,保證了小農經濟內部的組織、協調和管理得以順利進行,從而保證了家庭這個中國傳統社會的基本經濟─生產單元變得牢不可破。
但是,另一方面,家庭又只是中國傳統社會的基礎價值,而不是最高價值。因為在“小農經濟”之上,畢竟存在著一個高高在上的“大國政治”。所以,按照儒家的“家——國——天下”的價值譜系,“大同”必然在“小康”之上,“天下為公”必然在“天下為家”之上;孟子說:“禹疏九河……八年于外,三過其門而不入。”因此,中國一向存在著毀家紓難、大義滅親的傳統。“家”固然是傳統中國的基本價值,但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這個基本價值也可以——且應該被超越。
▍從家到國,從“五四”到革命
農耕時代,家庭是最重要的組織單元。近代以來,社會組織的單位,社會組織的方式,被工業文明徹底改變了。大機器生產和經濟不可能再以家庭為中心,廠礦、公司、院校、軍隊和政府機關等社會單位取代家庭單位,國民經濟概念取代小農經濟概念,公民道德——而不是家庭倫理,日益成為新社會風尚的基礎,“民族國家”日益成為新的最重要的人類共同體。在列國競爭時代,一切現存的傳統社會,都必須以最快的速度轉型為新的“民族國家”,否則,就不可避免地面臨被殖民、征服和滅絕的命運。
在這個大背景下,1840年以來,中國面臨日益嚴峻的挑戰。經過19世紀后期的徘徊、掙扎和妥協,進入20世紀,中國開始急劇轉型,家庭的變遷,是這個轉型的一項基本內容。在這方面,五四啟蒙運動首開先河。這里,需要交代一下“五四”的一個前提,因為這個前提常被忽略。
1914~1918年的一次大戰,實際上,是歐洲中心地帶的一場內戰。戰爭迫使列強將很大部分中國國內市場,歸還給當時初生的民族工業。同時,戰爭導致世界范圍內對食品和原料需求的增加,這同樣刺激了中國的經濟生產。這樣,從1912年到1920年,中國現代工業的增長率達到13.8%。這個增長速度,直到1953~1957年(一五計劃時期)才被超越。與經濟繁榮同步的是城市化進程的提速,例如在上海,華界人口從1910年到1920年增長了3倍。
以此作為物質基礎,包括知識分子在內的一些社會階層,其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已經歷轉型。事實上,五四啟蒙的范圍主要限于城市知識分子和學生群體。它的反傳統主義精神之所以能在短期席卷意識形態領域,正是由于運動的主要參加者,其生活方式已基本擺脫了傳統綱常名教的約束。五四啟蒙不多不少,只是在相應的社會存在基礎上,完成了意識形態的分內工作。
五四啟蒙以“打倒孔家店”為旗幟,將個人從傳統倫理束縛中解放出來,傳統家庭首當其沖。圍繞家庭倫理,以《新青年》雜志為例,從1916年以后,陳獨秀、李大釗、吳虞、魯迅等,連續發表論文、隨筆、小說,排炮似的轟擊傳統儒家,特別是家庭倫理,以現代社會的個人為本位,全面解構傳統。
在這方面,巴金的長篇小說《家》,這部中國文學史上印數最多的小說,某種意義上可視為一部總結之作,它以“家”為焦點,全景式地反映了1920年代初的時代轉折和變遷。除去這種正面抨擊傳統大家庭的長篇巨制外,即使是那些娓娓講述親情的短篇佳什,也折射了那個時代對家庭的批判。例如朱自清的名作《背影》(1925年),以父子關系為主題,主要情節為父親到火車站送兒子北行,幫他看行李、找座位、買橘子。在這里,傳統儒家塑造的“嚴父”形象,已蕩然無存。
作者當時在北大讀書,經歷過啟蒙運動的新思想、新知識、新作風洗禮。兒子看父親,“總覺他說話不大漂亮”,“心里暗笑他的迂”,他以憐憫的目光注視、打量、反省,看到的是一個特別疼愛兒子、嘮叨、瑣碎、笨拙、老態的父親形象。這里展示的,與其說是一般意義上的所謂親情和人性,不如說是一個被五四啟蒙打垮了的父親形象,是傳統儒家父親的一個漸行漸遠的“背影”。在這背后,是新與舊、青年與老年、進化與保守、少年中國與老舊中國等一系列價值的對峙、沖突和互動。子輩正在超越父輩。
家庭倫理是五四時期的大問題,易卜生的戲劇《傀儡家庭》(后譯作《玩偶之家》)曾風靡一時,并出現一批“娜拉”式的社會問題劇和社會問題小說。1923年底,魯迅在北京女子高等師范學校發表演講,題目是《娜拉走后怎樣》。走出傳統家庭的“娜拉”,作為個人,面對新的復雜社會環境,將向何處去?魯迅的這個問題,已經隱含了對“五四”的超越。
像娜拉那樣,走出傳統家庭,只是“打碎”的方面;另一個方面是“重組”,即擺脫綱常名教的個人,以新的原則重新聚集。這個工作,從五四后期就已開始了。各種青年知識團體,如學生救國會(1918年5月)、國民社(1918年10月)、平民教育講演團(1919年3月)、少年中國學會(1919年7月)等相繼成立。其中,少年中國學會規模最大,“少年中國”就是“新中國”,它以創造“適合于20世紀思潮之少年中國”為宗旨,兼收并蓄了各種政治傾向的知識分子。打碎─重組的過程橫跨了五四啟蒙與中國革命兩個階段。因此,盡管從同仁社團到政黨組織只有一步之隔,但這一步邁出去,五四啟蒙運動就被跨越了。
▍舉國體制盛極而衰
一般講,個人、家庭、社會、國家四個層次,構成人類共同體的內部結構。“五四”以后,個人走出家庭,在社會這個層次稍事停留,組成各種社會團體,接著便進入國家層次。因此,在“五四”之后,很快就是國民革命,先是國共合作,后是國共內戰,要建立的都是各自的現代國家——對于國民黨,是“民族國家”;對于共產黨,則是“人民國家”。但這個“建國”的進程,卻一再被日本所阻撓和打斷。從濟南事變(1928年)到九一八事變(1931年)和華北事變(1935年),直到七七事變(1937年),大半國土淪陷,中華民族自1840年以來所面臨的亡國滅種的大危機抵達頂點。為應對這個大危機,必須實行全國上下的總動員,必須實行“舉國體制”。所以,開始是“啟蒙”(五四),接著是“救亡”(抗戰),分別從不同的方向,超越了家庭及其倫理。
正是在中國革命時代,上述“打碎─重組”的過程宣告完成。在這方面,圍繞家國關系,最戲劇性地呈現了“打碎─重組”過程的是樣板戲《紅燈記》。李奶奶、李玉和、李鐵梅分別出于各自不同的破碎家庭,卻以階級、民族的恩仇情義和理念為紐帶,組成了非血緣的革命家庭,從而徹底顛覆了傳統家庭概念。以“大義”超越“親情”,是20世紀20~70年代中國革命的一個基本邏輯。但另一方面,《紅燈記》所表達的價值觀,在中國傳統文化的譜系中也并非毫無淵源。實際上,《紅燈記》的前身,電影劇本《自有后來人》的編劇沈默君,恰恰是從傳統戲曲《趙氏孤兒》獲得了部分靈感。只不過,為應對近代以來的民族危機,中國革命把傳統文化中的這種非常規邏輯長期化、普遍化了。
全民動員體制起始于抗戰,完成于1949年建國。需要指出的是,1949年建立的是“人民國家”(people-state),區別于一般所謂“民族國家”(nation-state)。“人民國家”以特定階級和階層為基礎,而“民族國家”則以特定民族為單位。這個人民國家以舉國體制實現了近代以來幾代人的夢想,完成了國家統一,建立了工業體系。在此過程中,個人、家庭、社會、國家四個層次中社會基本消失,家庭嚴重削弱,個人直接面對國家及其各個部門——社隊、廠礦、學校、機關、軍隊。
文革期間,中國在南、北兩個戰略方向,分別抗擊美、蘇兩個超級大國;在國內,則進行政權制度和意識形態大變革。舉國體制走向極致,所謂“七億人民七億兵,萬里江山萬里營”。家庭的地位和作用,被縮減到歷史最低點。
以尼克松訪華、中美緩和為標志,中國的國際戰略環境根本好轉,基本完成了自近代以來的“救亡”任務。從此,“救亡”階段將讓位于“發展”階段,長期實行的“準戰備體制”也將讓位于“和平體制”。
在這個大背景下,“現代化”主題取代先前的“革命”主題。改革開放,國家不斷從經濟、文化等領域退縮,社會逐步脫離國家,重新成長。知識分子回到五四啟蒙立場,在各種研討、講演、會議和書刊上批判中國傳統文化,家庭作為傳統文化的基本價值,也在批判之列。與此同時,從1980年開始,政府采取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家庭更加小型化。1980年代,是革命與啟蒙的某種混雜:情緒是革命的,理念是啟蒙的。這種混雜,一直延續到1980年代戛然而止的時刻。以此為轉折點,有關國家、社會的激情和想象迅速失落。
▍家,中國文化的最后堡壘
20世紀最后十年,社會運動恍如隔世,家庭價值被重新估價。1990年,電視連續劇《渴望》播出,以“好女人”劉慧芳為中心,通過幾個普通人的平凡故事,揭示愛情、親情、友情的細節和深度,創空前收視率。《渴望》的熱播,成為1990年代社會文化領域的一件盛事。而從中透露出來的,其實是人們對宏大的、超越個人經驗范圍的公共事務的深刻失望和厭倦。他們似乎發現,以家庭為中心的日常生活,蘊含著豐富而深長的意義和韻味。因此,宏觀地看,近百年來,中國的價值重心先是突然上升,爾后次第回落,從上述20年代以來的國家、社會回歸到家庭和日常生活。
從空間范疇看,如果說,對應于國家和社會的特定空間更多地是廣場、街頭、工地、廠房、會場、課堂等公共場所,那么,家庭則一般僅限于私人居室。而恰好在1990年代,家居裝修和房地產業陸續興盛,成為社會消費和國民經濟的熱點,就并非偶然,而有其深刻的社會心理和價值觀演變的基礎。人們感到,似乎只有在自家居室的掩蔽之下,在愛情、親情、友情的細節和深度中,才能獲得身心的慰藉、安寧和歸宿感。所以,這個作為家庭載體的居室,就特別值得營造和裝飾,值得刻意經營。在這種社會心理和價值觀的引導下,甚至公共空間也私人化了,最典型的表現,是1990年代興起的酒吧文化,那種幽靜、隱蔽、明暗相間的環境特點,其實意味著以往公共空間的瓦解。
隨著價值重心的回落,“大同”理想漸行漸遠,“私”的觀念深入人心,私人、私密、私有,都與“家”密切相關。所以《禮記· 禮運》說:“大道既隱,天下為家。”私德超越公德,經濟領域的私有化與公共權力的腐敗并肩而行,它們在1990年代的蔓延與家庭價值的凸顯一樣,都是1980年代以后社會心理和價值觀演變的結果,在深層分享著同一個邏輯。
另一方面,1990年代又是中國社會急劇轉型的時期。社會結構、利益結構根本調整,個人命運升沉起伏,特別是1990年代后期,經濟衰退導致國企困境,幾千萬職工下崗,在缺少基本社會保障的條件下,卻并未造成大的社會動蕩,部分原因就在于,許多下崗職工的生計問題在家庭和親友的社會網絡中得到了改善和緩解。
與城鎮職工大規模下崗形成對照的,是1億到1.5億農民工進城務工,活最累,錢最少。支撐他們的同樣是家庭價值。民工勤勞節儉,含辛茹苦,很大程度上并不只是為了個人,而更多為子女、父母、兄弟姐妹,家庭是其辛苦奮斗的動力和目標所在。筆者小區附近有一建筑工地,常年懸掛一幅宣傳標語:“想老婆,想孩子,想安全。”也就是說,個人的生命安全之所以重要,很大程度上以家庭的重要性為前提。千里之外的家是維系人生意義的中心和尺度,這既是一種社會保障,更是一種心理保障。所以,“春運”成為中國獨一無二的現象。轉型時期,“家”成為中國傳統文化最后的堡壘。
百年中國,主要是家與國的更替和嬗變。國家、社會、家庭、個人四個層次,未來,是繼續下行,從家庭走向個人,走向真正的原子化社會,還是回歸社會和國家?這將決定中國的前景。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09年4月刊,原標題為“百年中國的“家”與“國””。圖片來源于網絡,如有侵權,敬請聯系刪除。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系本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