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明在《疫情、衰退與沖突下的中國經濟新發(fā)展》一文中指出,不平衡復蘇是疫后經濟的主要特征。在國際層面,不平衡復蘇可能使得發(fā)達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之間的差距、高收入和中低收入群體之間的差距進一步拉大;在國內層面,不平衡復蘇則反映在消費復蘇滯后于投資,需求端復蘇滯后于生產端等現象上。經濟政策需要及時回應這樣的不均衡復蘇現狀。
疫情導致的國際局勢震蕩,以及不平衡復蘇給全球經濟帶來的隱患,使得加快“向內”調整經濟成為應對外部環(huán)境不確定性的必要之舉。張平和嚴鵬指出,制度改革和新型舉國體制可以為實現國民經濟的良好運轉開拓新的空間。張平在《創(chuàng)建“消費 – 創(chuàng)新”新循環(huán)》一文中指出,過去三十多年來的出口導向工業(yè)化發(fā)展模式已無法繼續(xù)維持,轉向以國內循環(huán)為主的發(fā)展模式是符合經濟發(fā)展客觀規(guī)律的戰(zhàn)略選擇。但要真正完成從出口導向工業(yè)化到“消費 – 創(chuàng)新”循環(huán)的轉型,必須建立起與轉型目標相匹配的制度激勵和宏觀資源配置體系。嚴鵬的《培育制造業(yè)生態(tài)體系:工業(yè)史視角下的“雙循環(huán)”》一文則從工業(yè)史的角度指出,全球化具有周期性特征,在本輪全球化擴張周期難以維持的當下,中國應該正視逆全球化威脅,重構經濟發(fā)展模式。在當前環(huán)境下,構建制造業(yè)生態(tài)體系對發(fā)展“國內大循環(huán)”意義重大:完善的工業(yè)體系一方面可以創(chuàng)造更多的產業(yè)內需求,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應對發(fā)達國家可能發(fā)起的技術封鎖。新型舉國體制應該在產業(yè)生態(tài)的培育和關鍵技術的創(chuàng)新上發(fā)揮引領作用。
打通國民經濟的良性循環(huán)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突破外部需求下降給中國經濟發(fā)展帶來的瓶頸,但已經深度卷入全球經濟體系的中國同樣需要對國際環(huán)境進行積極管理。在 2016 年特朗普上臺以及 2018 年美國發(fā)起貿易戰(zhàn)之后,高柏在本刊發(fā)表文章分析了出現逆全球化趨勢的政治經濟機制,以及中國為了應對內外變化所需要采取的國內調整。在本期中,高柏的《走出薩繆爾森陷阱——打造后全球化時代的開放經濟》一文則提醒我們進行國際調整的必要性。高柏認為,冷戰(zhàn)結束后,中國極大地發(fā)揮了比較優(yōu)勢,實現了經濟的快速增長;但僅從比較優(yōu)勢角度理解國際貿易,容易忽視國際貿易秩序和國際貿易利益分配的變化,以及其對各國國內政治及對外政策的影響。未來中國應該學習如何通過調整貿易利益的分配,實現減少國際沖突、增強合作的目標,進而為中國未來的發(fā)展創(chuàng)造更有利的外部環(huán)境。
在后冷戰(zhàn)世界格局發(fā)生巨大變動、全球經濟進入新的動蕩期的當下,中國經濟發(fā)展所面臨的空前復雜的內外部環(huán)境,已經遠遠超出了傳統學科的認知和解釋框架。中國經濟該如何逆風而上,不再是一個單純的經濟學、發(fā)展學問題,而成為一個橫跨政治、經濟、社會、國際關系等多學科、多領域的綜合性問題。回答這一復雜、全新而急迫的問題,需要中國社會科學界創(chuàng)建新視角、新理論、新范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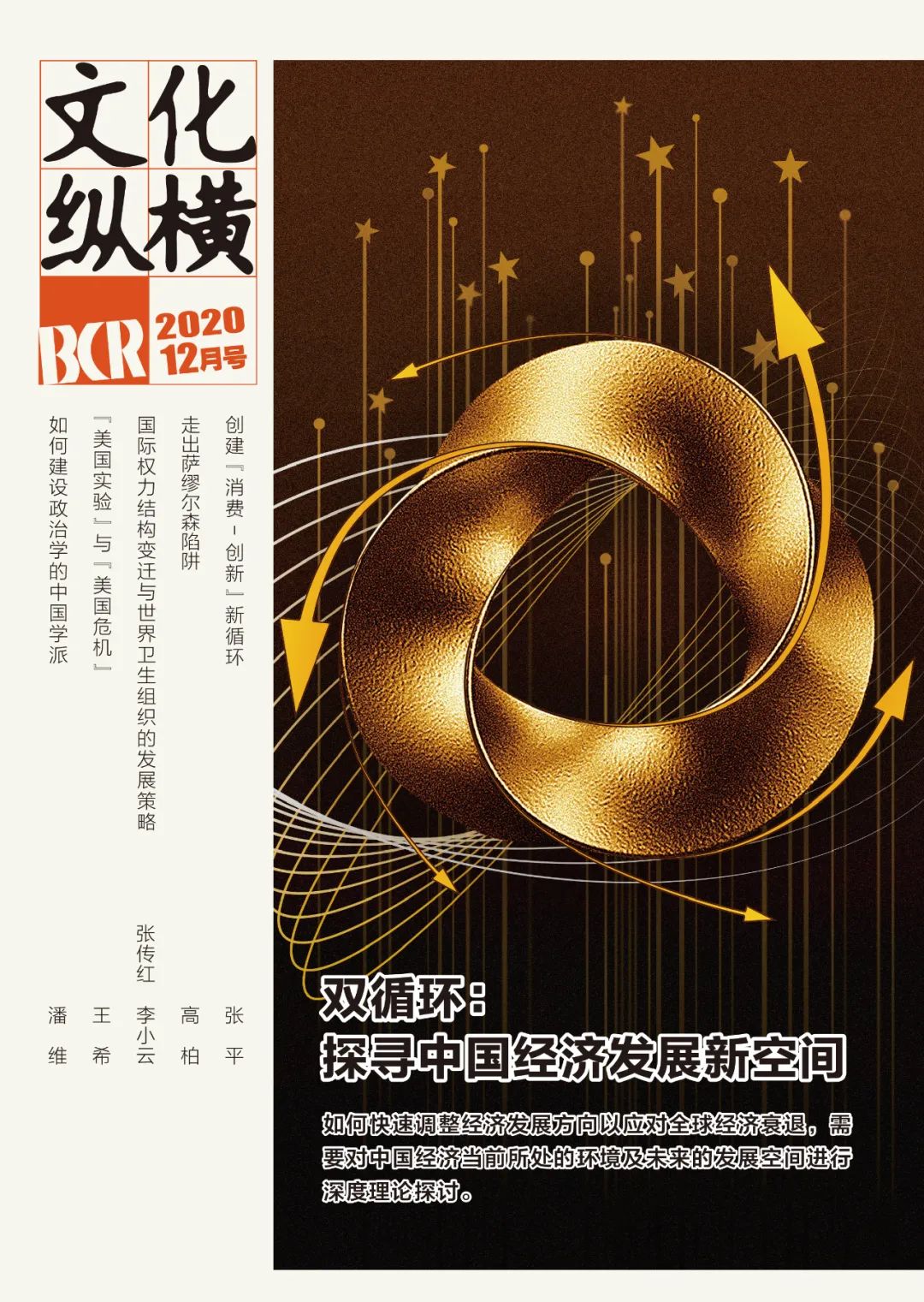
——《文化縱橫》2020年10月新刊手記
中美關系正發(fā)生突變,且似乎不以中國人的主觀意愿為轉移。
從貿易戰(zhàn)到新冠疫情的污名化,從關閉休斯頓總領館到南海軍演,從打壓中國企業(yè)到在香港、新疆、臺灣問題上的干涉內政……中國人觀察到,無論如何釋放善意,美國統治集團內部已經形成了一種相當堅決的意志——與中國脫鉤,遏制中國。
中美關系的突然轉變,將導致中國和平崛起的外部環(huán)境發(fā)生實質性改變,改革開放以來形成的“和平與發(fā)展”時代主題的判斷,中國發(fā)展“戰(zhàn)略機遇期”的判斷,以及建立其上的中國國家內外發(fā)展的戰(zhàn)略指導方針,都將不得不進行重大的調整。
對此,必須有充分的物質與心理準備。
▍中美關系突變的三大原因
中美關系的突變,可以從地緣政治、大國競爭等多個維度進行分析,但當代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不平衡性,乃是這一矛盾關系發(fā)生突變的根本原因。自資本主義誕生以來,尤其是近200年來,差不多每隔30年,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便會發(fā)生一次緣于其不平衡性而導致的秩序調整,“一戰(zhàn)”、“二戰(zhàn)”、冷戰(zhàn)以及今日中美新冷戰(zhàn),莫不如此。
在秩序調整期,世界進入一個明顯的動蕩期,新的秩序只有等待舊有矛盾沖突能量釋放完畢之后才可能重新建立。其間的摩擦、對立、遏制甚至戰(zhàn)爭,都是可以想象的。
導致中美矛盾突變的原因多種多樣,從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不平衡性角度分析,則有以下三大原因:
首先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資本主義經濟運行的周期性規(guī)律不斷演變?yōu)橐淮未蔚纳a過剩危機,以及系統性的金融危機。2008年金融危機雖然被G20機制采取的各種措施抑制住了,但各國經濟的內在結構性問題卻未能獲得根本解決。金融危機之下,世界經濟板塊格局重組,美國利用貨幣發(fā)鈔國地位對全球財富的轉移機制、利用虛擬金融經濟對各國實體經濟的掠奪機制,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削弱,以美國為中心的全球財富循環(huán)機制被打破,利用外部資源解決內部矛盾的回旋空間大大縮小。由此導致美國內外矛盾的不斷加劇。
其次是中國經濟板塊的崛起。中國經濟的崛起,是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不平衡性的典型表現,在全球范圍內配置流動的資本、技術、信息、勞動等經濟要素網絡中,中國崛起導致諸要素位置排序日益朝向有利于中國的方向變動,國際貿易、投資、生產中的利潤分配格局發(fā)生日益有利于中國的變化。由此導致本來由西方國家主導的世界經濟網絡受到極大的擾動,美國秩序遭受巨大沖擊。當代國際政治的動態(tài)關系,根本上決定于國際經濟的動態(tài)關系,經濟關系變了,政治關系一定隨之發(fā)生變動。
第三,以智能技術為代表的新技術革命,是導致世界格局變動以及中美沖突的深層原因。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常常帶動新技術革命,以降低成本、提高效率,進而擺脫危機。從上個世紀70年代以來,美國的信息技術革命便不斷演進,并在此基礎上向智能化、自動化快速發(fā)展。尤其是金融危機以來,這一技術變化趨勢日益明顯,其直接結果,是少數高科技企業(yè)利潤率日益高企,而多數低技能勞動者則越來越被排除在現代制造業(yè)的門檻之外。美國的右翼民粹主義和排外思潮,美國民意對中國搶奪美國百姓工作的誤解,均與其背后發(fā)生的新技術革命相關。
上述三種原因,是導致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不平衡的根本原因,也是導致中美沖突的根本原因。當這三大矛盾運動積累到一定階段時,量變就會變成質變,矛盾沖突便會益發(fā)尖銳而不可調和。中美關系的全面沖突,即是這三大矛盾運動發(fā)生質變的突出標志。
▍美國內部政治經濟失衡與中美沖突
中美關系突變,同時也是美國內部經濟政治失衡的集中表現,很大程度上,它是美國內政的外部延伸。
導致美國內部政治經濟失衡并殃及中美關系的,大致有以下幾種因素:一是美國日益嚴重的貧富分化,不斷加劇內部的社會撕裂。多種調查數據和現場觀察都表明,美國財富分配差距已經到了令人無法忍受的程度,無論與美國歷史比較,還是與其他西方發(fā)達國家比較,當代美國的貧富差距都是前所未見的。貧富分化的加劇,導致社會矛盾沖突沿著不同種族、階級、民族之間的分界線展開,并集中反映到互不妥協的政黨政治之中。二是美國人種比例的變化,白種人所占人口比重日益下降,并可能在不遠的將來成為絕對意義上的少數,這加劇了盎格魯-撒克遜等白人族群的焦慮,并催化了民粹主義與民族主義,也催化了共和黨人的極端保守主義傾向,同時催化共和、民主兩黨的尖銳對立。三是美國經濟的金融化和去工業(yè)化趨勢。由于技術進步和全球化,同時也由于美國新自由主義經濟思潮不受節(jié)制,美國大量工業(yè)轉移海外,虛擬經濟大規(guī)模興起,這直接導致了工業(yè)制造業(yè)崗位的大規(guī)模流失與財富的不平等分配。
上述幾重因素,已經成為美國內部矛盾的結構性因素,無論主觀如何努力,客觀情勢已經幾乎不可逆轉。這些結構性矛盾的疊加,加上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不平衡性的推動,美國的內部矛盾就變得特別突出、特別尖銳,并很容易為政治勢力操縱,成為中美矛盾沖突的內部溫床。
▍內外矛盾交集,當前的美國特別危險
當前的世界,正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舊秩序解體,新秩序遠未建立。舊秩序解體過程是矛盾沖突集中爆發(fā)時期,同時也是特別危險的時期。
過渡時期的危險,主要來自新興力量的興起與傳統霸主維護霸權的行動。在核時代,確保相互摧毀通常會避免核大國之間的直接戰(zhàn)爭,矛盾沖突更多地會以代理人戰(zhàn)爭或資本主義世界體系邊緣國家的直接沖突為表現形式。但是當一個衰落中的帝國內外矛盾特別集中,其維護霸主地位的愿望特別強烈時,大國之間爆發(fā)直接沖突的可能性就會明顯上升。
今天的美國,內部矛盾催生了特朗普的民粹主義,這一潮流如果與軍工資本利益集團結合,很容易產生法西斯主義的軍事冒險行動。而外部世界,由于多極格局尚未形成,且世界的經濟中心(亞太)與軍事中心(美國)相互分離,美國挾其龐大的軍事力量,在缺乏外部力量制衡的情況下,也很容易選擇軍事冒險,通過軍事訛詐的形式,獲取更多經濟利益。
今天的世界大變局中,中美矛盾正日益上升為主要矛盾,中美矛盾的主要方面則無疑是美國。美國日益加劇的內外矛盾,導致今日美國特別危險,這一點,不會由于美國統治集團領導人的更迭而改變。對此,中國人必須有清醒的認識。
在邁向大市場的過程中,小農戶的生活經歷了從工作、經濟收入的變化,到社會關系網絡的重構,再到價值觀念的不斷重塑,較之過往“面朝黃土背朝天”的狀態(tài),不確定性急劇增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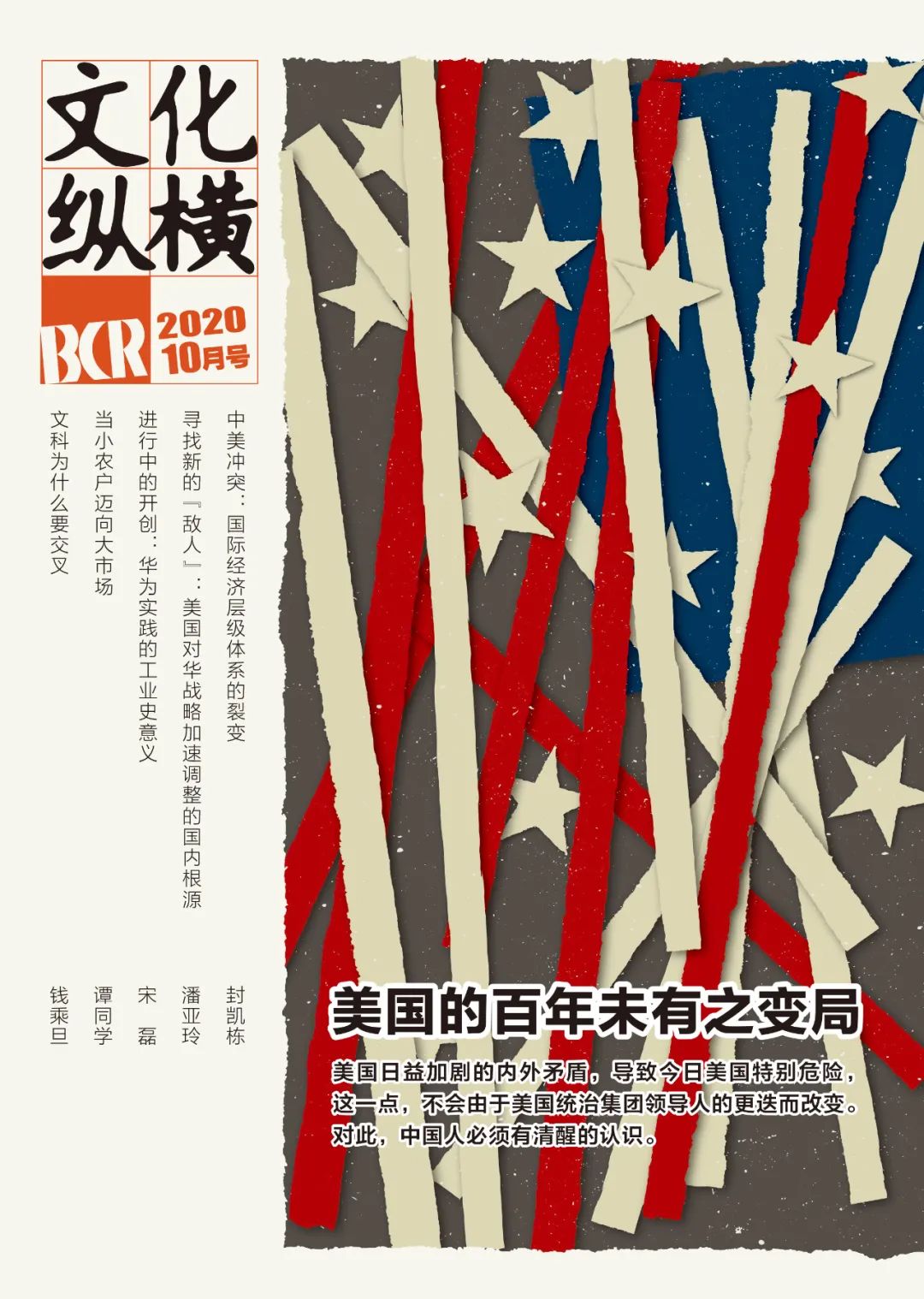
思想理論創(chuàng)新的核心任務是什么?
——《文化縱橫》2020年8月新刊手記
▍危機呼喚思想理論的創(chuàng)新
2020 年的新冠疫情危機,正從公共衛(wèi)生危機演化為經濟危機、社會危機乃至政治危機,并逐漸推動地緣政治危機浮出水面。危機帶來焦慮與困惑,其中最大的焦慮是未來的不確定性。人們以往熟知的知識經驗及思想理論范式不斷喪失解釋力,尤其是冷戰(zhàn)結束前后形成的新自由主義理論范式更是面臨著急劇變化的現實世界的尖銳挑戰(zhàn)。
新自由主義理論范式以“民主、自由、市場經濟”為關鍵詞,在蘇聯解體后形成了一套邏輯自洽的解釋體系,構筑了新自由主義的世界秩序的愿景與理想,并形成了世界范圍的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tài)霸權體系。然而自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機開始,新自由主義理論便不斷遭遇現實沖擊,其理論的思想邏輯和現實解釋力漏洞百出。尤其自新冠疫情危機暴發(fā)以來,新自由主義的理念及實踐更是面臨著破產的危機。
危機呼喚理論創(chuàng)新。重大的思想理論創(chuàng)新,從來與危機相伴而行。
對于中國的思想界而言,由于中國工業(yè)化、現代化進程的時間的高度壓縮性,在幾十年時間內要解決西方國家?guī)装倌陼r間中面對的問題,同時又由于中國幅員的廣闊及人口的眾多,中國遭遇的現代性問題是人類社會從未遭遇過的。因此,挑戰(zhàn)的尖銳性決定了理論創(chuàng)新的艱巨性,同時也決定了理論突破的現實可能性。中國問題的解決,很有可能就是人類問題的解決。
中國的理論工作者應該有這樣的思想自覺——隨著中國與世界的日益融合,隨著中國與世界日益無分內外,中國的問題即可能是世界的問題,世界的問題也必然是中國的問題。因此,中國的理論創(chuàng)新,必須以世界問題的解決為前提,必須與人類的問題意識保持同步。執(zhí)著于中國的獨特性,無助于中國正在展開的基于“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偉大實踐,中國必須在 21 世紀為人類社會貢獻新的普遍性價值。
?盡管疫情危機暴露了資本主義秩序的大量矛盾,但我們必須承認,今天的世界仍然處于資本主義時代。資本主義自 15~16 世紀萌芽以來,逐漸向世界擴展,形成了強大完備的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在資本、技術、組織、勞動、民族國家等諸多構成世界秩序的基本要素中,資本仍然是決定性的,資本主義在 300 多年的各種挑戰(zhàn)中,形成了由資本支配的經濟體系、政治法權體系以及上層建筑意識形態(tài)體系。
自馬克思主義誕生以來,社會主義運動的主要任務之一,便是分析與批判資本主義,為社會主義創(chuàng)造現實與未來的條件。今天的社會主義者,仍然面臨著分析批判當代資本主義的艱巨任務,沒有對當代資本主義的深刻批判,便不可能有社會主義的新的未來。
當代世界的資本主義,集中體現為金融資本主義,在物質生產、實物貿易以及為之服務的第三產業(yè)之外,有著一個獨立運動的資本形態(tài),它集中表現為虛擬資本的生產及交易行為,它不但已經脫離實物資本,而且反過來左右甚至決定實物資本的運動。這種金融資本主義發(fā)生發(fā)展的內在原理及動力機制,它的財富分配的效應,它未來可能的演變等等,并不為當代中國人所理解,也遠未納入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分析批判框架。當代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必須對金融資本主義做出深刻的闡釋與批判。
分析批判當代資本主義,還必須面對全球化這一資本運動的外部形態(tài)。伴隨著技術進步和產業(yè)的全球配置,資本日益全球化,它不斷跨越主權國家的疆界,重新界定資本與民族國家的關系,重新界定資本與勞動的關系。它導致工人運動不斷瓦解,勞動者日益喪失談判權;它也導致主權國家日益喪失稅源,不斷被資本權力所俘獲。與此同時,當全球化資本主義遭遇金融危機、新冠疫情危機時,逆全球化浪潮又開始興起,資本主義秩序日益顯現出民族主義、民粹主義、國家主義甚至法西斯主義的特征。資本主義的這種全球化與逆全球化交替出現的鐘擺現象,并不是第一次,它曾在歷史上反復出現。然而這一現象的內在運動機理、它的政治經濟后果,它對資本主義社會的影響,它對社會主義的意義,卻并未得到有效揭示。因此,分析批判當代資本主義,必須從微觀資本運動進入宏觀資本運動的分析,必須建立全球化時代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
要分析批判當代世界資本主義,就必須認真對待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當今世界資本主義時代仍然以社會主義為旗幟并現實運行的國家形態(tài),也是未來世界走向社會主義的現實實踐摹本。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核心特征,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運行體制。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的對立統一運動規(guī)律,決定了中國社會主義的根本性質。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一方面有著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tài),有著以共產黨領導為主要特征的社會主義國家形態(tài),有著以國有企業(yè)為主干的社會主義經濟基礎;另一方面,它還有著龐大的市場經濟運行主體,有著市場經濟所規(guī)定的產權秩序與分配秩序,有著市場經濟所影響的倫理價值與道德秩序。
中國當代的社會主義事實上面臨著雙重時代任務。一重任務是完成工業(yè)化與現代化,而與工業(yè)化、現代化最為匹配的經濟運行體制就是市場經濟,運用市場經濟所可能造就的先進生產力,將能夠推動中國社會邁入現代工業(yè)文明,克服并拋棄傳統農耕社會帶給中國的等級秩序、官僚主義、裙帶關系等封建主義遺毒。另一重任務則是在完成工業(yè)化的同時推動共同富裕,避免市場經濟所可能帶來的貧富分化、環(huán)境破壞、道德滑坡,并引導中國社會不斷向社會主義的更高級形態(tài)邁進。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即是當代中國這雙重時代任務所規(guī)定的有效運行體制。然而既然搞市場經濟,就不可能避免市場經濟中資本運動的邏輯,社會主義的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就有可能面對被資本力量滲透瓦解的局面。因此,指向未來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應該是既能充分發(fā)揮市場經濟的效率優(yōu)勢,又能夠充分發(fā)揮社會主義共同發(fā)展、公平分配的優(yōu)勢,二者的對立統一運動,將決定中國社會未來的性質。
對于中國思想界而言,當前最重要的任務之一就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政治經濟學,包括這一體制下的國有企業(yè)、外資企業(yè)與民營企業(yè)的相互關系,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產權關系、分配關系與交換關系,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國家 – 資本 – 勞動的關系,等等。
沒有對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政治經濟分析,就不能準確認識當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也就不可能深入分析批判當代世界資本主義。這一重要的理論工作,在疫情危機的世界時刻,顯得尤為緊要與迫切。
▍重建價值的巨大希望
自以市場經濟為導向的改革開放興起之后,中國社會經歷了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巨大轉型,伴隨著財富的快速增長,人們普遍渴望一種新型的價值倫理,以使當代中國人能夠在物質豐裕的時代獲得心靈上的安頓。這種價值倫理的訴求,在上層建筑領域體現為一種可以統領當代人生活的意識形態(tài),在普通人日常生活中則體現為一種人與人之間彼此相處的健康生活倫理。
重建價值,是時代緊迫而巨大的呼喚。而對此訴求的可實現性,多數人的感受是悲觀大于樂觀。然而這次抗疫中所展現出的中國人民的精神風貌,卻讓我們看到了重建價值的巨大希望。
從人民子弟兵第一時間出動,到各地醫(yī)療機構馳援武漢;從志愿者的自發(fā)有效的行動,到民營企業(yè)家群體大規(guī)模的公益捐贈;從醫(yī)護人員冒著生命危險的逆向而行,到雷神山、火神山醫(yī)院建設中建筑工人的勤勞身影;從商業(yè)公司高效的物流配送,到各地支援武漢的物資運送大軍;從基層社區(qū)工作者辛苦的工作,到武漢人民令人難以置信的自律精神……
危難面前,中國人民整體迸發(fā)出的精神能量令人驚嘆不已,它讓以往那些評價中國人國民性的詞匯頓時失靈,什么“一盤散沙”、什么“丑陋的中國人”、什么“冷漠自私”……
疫情洗禮中,武漢變身為一座英雄的城市,中國人升華為一群足可自傲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英雄人民。以這樣的民族形象,中國人就不用再忌憚令人恐懼的“挨罵”問題,以這樣的民族品質,中國人就有可能在正劇烈展開的國際競爭中贏得勝利。它們遠比GDP的競爭、軍事武器的較量能帶來更大的征服力。
▍制度的優(yōu)勢與治理的短板
疫情的成功防治,使我們看到中國社會主義制度與體制的巨大優(yōu)越性,也使我們看到公共衛(wèi)生危機中暴露出的我們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短板。
疫情處理中,人們通常所說的“舉國體制”發(fā)揮了巨大的作用,而所謂“舉國體制”,絕不單純是一種體制機制,而是其背后深刻的社會主義制度與社會主義價值觀的決定性影響。它至少包含著如下幾個面向:首先是一切為了人民、以人民為中心的共產黨的立黨宗旨,這種宗旨在重大危機的政策抉擇中,會自動逼使決策者選擇以人民的生命安全與人民的利益為第一位,而不會屈從于利益集團的狹隘訴求。其次是共產黨的堅強領導,經過90多年的革命與建設的實踐,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力已經形成貫穿中央與地方、中心與邊疆、全國上下一盤棋的強有力的組織力和動員力。第三是下沉到村落、社區(qū)、商業(yè)樓宇的黨的基層組織網絡體系,尤其是十八大以來的基層黨組織的重建工作,以及網格化管理等社區(qū)治理體系的建設,使得危機之下的中國社會不會由于市場經濟導致的個人原子化,而影響需要強有力組織行為才能完成的抗疫行動。第四,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40年建設中,社會生活中發(fā)育出充滿活力的民營企業(yè)家群體與公益組織群體,他們在抗擊疫情的過程中高效靈活,彌補了政府組織科層化管理中難免出現的疏漏和不足。
與此同時,我們也看到了抗擊疫情中出現的治理問題。從初始階段在疫病防控與地方經濟社會穩(wěn)定之間的猶豫不決,到抗疫展開階段地方行政系統效能的低下;從疫情壓力下仍然頑強表現出的形式主義與官僚主義,到全國上下不分具體情況的“一刀切”式的管理;從許多官員身上表現出的明顯的能力不足,到面對洶涌而來的網絡輿情時宣傳管理部門的手足無措……
正如領導人所說,“這次抗擊新冠肺炎疫情,是對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疫情防控中暴露的這些短板,概而言之,是國家治理的現代化任務沒有完成,是工業(yè)化、信息化、城市化、市場化時代,傳統的農耕社會形成的文化慣性,未能同步在社會治理中實現現代化的轉型。
當代中國的社會治理,一方面不能丟掉共產黨的優(yōu)良傳統,另一方面必須進行與時俱進的現代化改造,其主要標志,就是社會治理的科學化與法治化,它要求精細合理的分工、上下對稱的信息溝通、重要決策的依法依規(guī)、集中統一領導與個人能動性的有機結合,等等。而所有這些現代化管理的方方面面,都顯現出我們國家、政黨和人民普遍缺乏的現代治理的技藝和文化的短板,需要下大力氣進行改造升級。回溯兩個多月的疫情防治,給予我們的最大啟示,就是要將制度自信和道路自信,與國家治理的現代化改造緊密結合起來。沒有制度自信,我們將喪失根本優(yōu)勢,沒有現代化治理的改造升級,我們就將無法邁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行列,也將無法有效地參與全球化時代的國際治理。
▍疫情正在對世界格局產生深刻影響
當代國際競爭,正面臨兩大懸而未決的問題:一是以中國為首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與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道路誰勝誰負的問題;二是疫情可能誘發(fā)全球性經濟大危機的情況下,人類社會將面臨什么樣的前景。第一個問題的答案已經接近明朗,經過兩個多月的頑強奮戰(zhàn),中國的制度、體制機制、人民的品格、中國的話語,正產生不可阻擋的沖擊力與說服力,它將在廣大第三世界與許多中等發(fā)達國家中產生巨大的影響力,它將使膠著不下的東西方競爭的局面迅速明朗化。
而第二個問題則陰影密布,前景令人擔憂。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世界范圍內形成了 G20機制,世界大國共同攜手克服金融危機,以避免上個世紀世界性戰(zhàn)爭的陰影。但特朗普上臺以后,美國奉行“美國第一”,大肆破壞國際合作機制,通過貿易戰(zhàn)、退出國際條約等方式,近乎瓦解了G20等國際協調機制,加深了民族國家之間的鴻溝與不信任。當疫情來臨,并可能誘發(fā)新的經濟大危機之際,新的國際協調與國際合作將顯得異常重要卻也異常艱難,防治疫情這樣尤其需要國際合作的重大事件,目前看不到大國之間打破偏見攜手合作的可能性。疫情危機,如果疊加上經濟危機,人類的前景令人憂慮。對此,我們必須做好充分的準備。
《文化縱橫》編輯部
2020年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