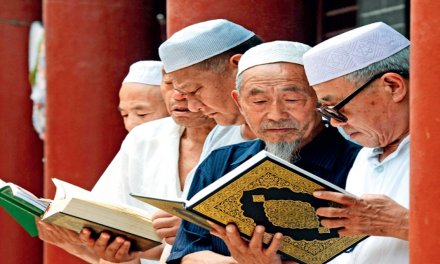馬海云
本文關注的是18世紀清代內地對“穆斯林”即“回回”或“回教”的三重文化表述及其背景。這三重文化表述分別源自漢人士紳、滿人皇帝以及回民知識分子。每一種文化表述都有其特定的政治、歷史、文化和社會背景:漢人士紳有關“回回”的話語根植于漢語歷史文獻對古代西北族群——從晉代的胡人到唐代的回紇/回鶻——的記憶、想象和傳承;隨著清代西進擴張,中原士紳有關“回回”的文化想象與歷史記憶相聯系并被賦予新的意涵。而滿人皇帝對內地“回民”的認知和界定則基于“族-民”這樣一個政治、法律和行政劃分,即作為信仰“回教”的“回民”和信奉“儒釋道”的“漢民”一樣,都是法律意義上的內地(臣)“民”。清代疆域的變遷及其在內地引發的文化震撼深刻地影響了清代回民的智識活動,“漢克塔布”或“漢書”(或所謂的“以儒釋伊”)便是這一歷史進程的互動產物。尤其是回民知識分子對“回教”的闡釋和正名更是突出反映了清朝領土擴張之后在內地漢、回群體的不同影響。
回民為“回”:漢人士紳的“恐回癥”
清代漢人士紳對穆斯林和伊斯蘭的表述和話語同其歷史文化記憶和想象息息相關。盡管中國穆斯林的來源多元,但漢文史料中有關“回民”的記述卻與抽離了“伊斯蘭”的西北邊疆歷史族群——“回紇”或“回鶻”——相提并論。這一趨勢在明末就已成型。如顧炎武(1613?1682)在《日知錄》的“外國風俗”中便將明代的“回回”和唐朝的“回紇”、“回鶻”以及《元史》中的“畏兀兒部”等同起來。他甚至認為“畏”就是“回”、“兀”就是“鶻”,而“回回”就是回鶻的音譯。顧炎武將這一漢文歷史中的非穆斯林異族同明代的回回穆斯林直接嫁接,并且指責回民食牛的風俗。明代漢人士紳的“回回”論甚至根本沒有提到或者知曉“伊斯蘭”,而只是延續了農耕士紳階層對邊疆歷史、文化和族群的解讀。隨著其著述的流傳、收藏(尤其是《四庫全書》),顧有關“回回”的言論成為清代漢人士紳認知和攻擊“回回”的基礎,如《清稗類抄》和《圣武記》就呈現出不同程度的關聯。
盡管文化偏見在明末清初的中原士紳之間屢見不鮮,對回民的群體性和政治化攻擊卻在18世紀達到了高潮。也許是面對滿人的異族統治和清朝通過改革羈縻地區不斷擴大內地領土和增加新的“內地”臣民,漢地士紳很快掀起了“禁回”或“反回”運動。尤其是在雍正“改土歸流”之際,山東巡撫陳世倌(1680?1758)在1724年上奏朝廷, 指責內地“士紳”信奉回教。這表明當時清朝的內地官僚體制不僅僅限于漢人士紳。的確,《清史》列傳中的很多回回武將基本出自“回部”。陳此時對內地回教的攻擊顯然是投機主義式的,是想把朝廷的“改土歸流”行政改革異化為文化同化政策。
陳對回教的指責上升到政治的高度:回教不敬天地,不祀神衹,不奉正朔;他甚至將回民日常生活上升到國家認同和叛國行為,即回民居然“另立宗主,自為年歲”。這些指責同此時回民在內地“嵌入式”的居住形態有關。同顧炎武一樣,除了攻擊回教食用牛肉等風俗之外,陳甚至抱怨回民之間的民族團結,即其“同心協力”。陳呼吁朝廷勒令回民官員“出教”,這表明在18世紀內地士紳以回民的宗教和文化為借口而掀起的反回運動更多是出于官場斗爭的需要,以達到排除異己之目的。
五年之后,陳世倌對回教的攻擊由風俗習慣延伸到經濟行為。他在1729年的一份奏折中公然指責回民的社會和經濟網絡,即回民千里不持糧就能游走各地,而且其商業據點遍布水陸要津。陳認為回民作為“內地百姓”不得信奉回教,違者以“師巫邪術律”治罪。很顯然,陳世倌將清朝的內地政治臣民群體儼然等同于漢文化族群。
幾乎與此同時,鎮壓了羅卜藏丹津事件的川陜總督岳鐘琪(1686?1754)也呈交類似奏折。他將陜西渭南的回民同販鹽、打架斗毆、偷盜、賭博、酗酒等行為相提并論。在奏折中,岳氏起初建議增設“專門針對回民”的科條。但害怕這樣的異視會導致回民“變心”而只好作罷。但是,作為補充措施,他建議強化“牌頭甲長”制度,普及“回民義學”。換句話說,岳鐘琪的民族歧視政策無法推行,便寄希望于漢化文化政策。繼陳世倌、岳鐘琪之后,安徽按察史魯國華也指責回民修建“清真”和“禮拜”寺院。他遵循陳世倌將內地“臣民”等同于“漢民”的邏輯,聲稱回民作為“盛世之民”不應信奉回教,他甚至建議以“左道惑眾律”治罪回民。對于戴白帽的回民,魯要求以“違制律”進行處罰。
如果說這些18世紀初期的奏折和言論反映出漢地士紳趁著邊疆改制之際推行文化擴張,那么18世紀末出自山東小知識分子的文化評論則赤裸裸地攻擊和威脅大清的領土完整。1780年,山東巡撫富察國泰(??1782)上報一個文字獄事件。壽光縣縣令勞敦樟在處理一起案件搜家時,意外地發現了一篇署名“魏塾”的、關于西晉江統《徙戎論》的評論。國泰之所以認為此事關系重大,是因為他在魏塾的評論中發現后者將“當今回部”等同于“晉之五部”。根據魏塾的招供,他認為晉惠帝沒有采納江統徙戎的建議,最終導致了“五胡之亂”。當清朝官員斥責魏塾為何將晉之“胡部”同清之“回部”相聯系時,魏塾供認說他認為當今回教就是“外國來的”。也就是說,魏塾將清朝剛剛征服的新疆當做外國,把清朝的回部等同于晉代的胡部,把大清的西進宏業視為亂華行為。
上述奏折、建議或評論勾勒出18世紀漢人士紳的“禁回”或“恐回”浪潮。有意思的是,這些“禁回”言論無一例外地將回教同早先漢文史料中的邊疆異族相提并論。尤其在魏塾案件中,他將清朝的回部視為伊斯蘭教產生之前的晉代胡人。這些攻擊回民的政治和文學言論恰逢清朝的“改土歸流”。當清廷從雍正年間開始頻頻過問廣西、臺灣、福建、甘肅等地改土歸流后的“新地”或“新疆”的“民情”、“民風”之際,內地漢人士紳趁機將“漢俗”同朝廷的行政改革捆綁起來。事實上,正如清朝皇帝所揭示的那樣(見下文),清朝在內地并沒有將“漢俗”等同于“民俗”,也沒有將“民人”等同于“漢人”。
回民為“民”:滿人的臣民政策
作為不斷擴張的大清帝國,清朝對境內不同宗教和文化之間的交流和沖突,尤其是對不同文化群體之間的誣陷和攻擊保持著高度的敏感和警惕。清朝對“回民”和“漢民”的政策始終一以貫之地以政治和法律的平等身份看待,而不是以文化和宗教差異而異視。如北京牛街禮拜寺的康熙圣諭所表明的那樣,在漢人官員誣告回民在清真寺“夜聚明散”、圖謀不軌時,康熙圣諭清晰地表明了清朝皇帝對回教文化的熟悉以及對內地不同文化臣民的一視同仁。在康熙看來,那些不食“君祿”的回民尚且知道一日五次拜“主”、贊“圣”及“報本”,并從政治忠誠度和感恩戴德程度上評論二者:“漢不及回”。
雍正更是察覺到漢人士紳對回教的刻意攻擊和誣陷。在回復陳世倌的圣諭中,雍正指出,回民作為登記入冊的“民”,早已遍布各省州府。回教作為世代信奉的宗教,如同漢人的“家風土俗”。雍正同時指出,回民由于“籍貫”不同也有不同的風俗習慣。甚至針對那種試圖把回民罪犯化的企圖,雍正強調了回民不等同于亂民。雍正由此重申,回教和回民在“中國”即內地的存在“毋庸置疑”,并特別駁斥了陳世倌企圖異端化回教和罪犯化回民的企圖。這種企圖在雍正看來,無疑會敗壞朝廷在“藩邸”好佛的名聲。換句話說,雍正將陳世倌對回教的攻擊看作是對大清軟實力的破壞。
雍正也同樣駁斥了魯國華的謬論并指出“異視”回民和回教的政策在歷朝都不存在。針對其對“清真”和“禮拜”寺院的異端指責,雍正指出,正如各地漢人的拜神一樣,回民也僅僅是拜主,只不過這些宗教活動并沒有記載在漢人的“祀典”里。雍正由是懷疑魯國華對回教的攻擊懷有不可告人的目的,并質疑在訓誡陳世倌之后,對回民的誣陷奏折卻為何仍舊屢見不鮮。雍正因此指出,魯國華對回民的惡意攻擊要么是公報私仇,要么是故意擾亂國家,據此將魯國華撤職查辦。在看到眾多誣告回民的奏折之后,雍正直言回民“若較之與漢,百分中不及一分”,朝中回民官員眾多,作為良民是其“本心”。最后,雍正要求官員要對回教和回民一視同仁,不得“異視”,需以“治眾者治回民”。這和雍正改土歸流、甚至清朝總體的民族政策相適宜,即“齊其政而不易其俗”。
征服新疆之后,清朝更是對江南心態和犬儒文字保持高度的警惕。乾隆發現《明史》中涉及回民回教的“回”字,皆有“犬”旁。在1775年下令從所有史書中去除這種侮辱性文字。魏塾有關回教的評述,在乾隆看來更是“妄批”。誠如富察國泰建議,乾隆認為魏塾的罪行實屬“大逆”。換句話說,對朝廷而言,最大的分裂主義言論來自諸如魏塾這樣的山東內地儒生。
清朝的這些駁斥和懲罰并不能視作朝廷對“伊斯蘭”和“穆斯林”的保護,而是將“回民”作為內地臣民公平對待。從康熙到乾隆的政策說明,清朝對臣民的界定是以政治和法律為依據,而非文化和宗教。即無論信奉何教,內地臣民首先是清朝的“民”,回民如此,漢民亦如此。換句話說,清朝在內地并沒有以漢文化同化所有臣民;清廷也沒有認為在“回民”的“回”和“民”之間有沖突。事實上,清代內地臣民政策遵循了這樣一個模式,即“族-民”模式。無論是“回民”或“漢民”,還是改土歸流的“疍民”或“番民”,都是大清的臣民。這一“族-民”模式將臣民的宗教文化屬性如“回”或“漢”與其政治、法律身份“民”有機地統一起來,即尊重了臣民的不同文化實踐,也保證了不同文化背景臣民的政治、法律身份的統一性和公正性。這就解釋了為何清朝皇帝屢屢保護“回民”的原因,這里我們看到了一個類似現代“公民”或“國民”的概念和實踐。
回民為回民:“漢克塔布”
明末清初漢人士紳對回教的攻擊是對歷史上西北邊疆民族如“回鶻”和“回紇”偏見的繼續。自17世紀以來的回民知識分子早已熟知漢人士紳攻擊回教的淵源。與漢人士紳將回教和非穆斯林“回紇”生搬硬套的做法截然相反,回民知識分子的漢語著述即“漢克塔布”開始系統地闡釋回教并試圖去族群化。王岱輿(約1584?1670) 在其《正教真詮》一書中,對“回回”從宗教和哲學角度進行闡釋:
大哉回回,乃清真之鏡子,天地即彼之楷模也。萬物之擁護,真為全鏡之形;教道之搓磨,皆緣回鏡之光。夫回光有二:曰“身回”、曰“心回”。
身之回亦有二:曰“還復”也、 “歸去”也。
心之回亦有二也:人生在世,皆樂富貴而惡貧賤,遂染于二事??復思本來,急尋歸路,熔情欲而為天理,化萬象而反虛無,茲正心之回??果能復得其巢,既到此家,其無心之回也。無心之回,顯命源而得無極,體無極而認真主者,其回之至矣哉。
此后的漢克塔布著述中基本遵循王岱輿的解釋,對“回回”的哲學闡釋進一步深化和細化,如《回回原來》一書中將“回回”二字進行詞源學和詞義學上的解釋,如“字行內外俱如一,惟有一回采取中”。作者劉三杰、劉智父子將“回回”與此生和后世相聯系:
蓋塵世乃生人之客寓,幻途非久處之家鄉,故心懷常往,不忘本原,身雖在世,心實回焉??遵真主之明命,履至圣之真傳,則身回太極之清,性回無極之妙,成全正果,克登天闕,而得真主無疆之賜,此取名“回回”也。
為了消除漢人士紳對“回教”的族群化聯系,回民知識分子甚至以“清真”—— 一個漢人士紳比較熟知和尊崇的詞匯——來代替回教。值得指出的是,明清回民知識分子采用“清真”一詞指代“回教”不僅僅是因為這兩個字在漢文化背景下最大限度地闡明了伊斯蘭教;而且更重要的是,明代有關伊斯蘭和穆斯林的圣諭、御詩以及御賜官寺無不含有“清”、“真”或“清真”字樣。正如明末回回先賢王岱輿指出的那樣,“圣朝褒崇清真教”。他甚至將“清真”之名和朱元璋的御詩相聯系。根據王的說法,朱元璋對回教及回教圣人的評價極高甚至取名“清真”(“降邪歸一,教名清真”)。村田幸子從王岱輿的《清真大學》中看到了伊斯蘭教和儒教的高度融合:它將伊斯蘭教闡述為“清真”和儒家的經典《大學》并置,旨在表明兩者之間的共通共融特征。
清朝的回民知識分子繼續將回教泛“清真”化。事實上,清初以來許多回民學者的著述都含有“清真”標題。馬注(1640?1711)直接提及其著述《清真指南》是受到了王岱輿的《清真大學》的影響。馬注對伊斯蘭的研究也同17世紀末的清朝地緣政治變遷有關。根據馬注的記述,康熙帝于1679年在蠡城狩獵時,偶然看到一“清真閣”里面的“天經”而久久“不忍去”。三年之后,當西域使臣進獻天經之后,康熙要求禮部傳喚京城內外官員進行講解,但終不得要領之人。根據馬注的說法,康熙甚至在蒞臨五臺山之前的最后一天,還在景山等待能夠講解此經之人。正是這些滿人皇帝與西域回人的互動以及對回教知識的尋求,促使馬注在垂暮之年下定決心以漢語完成《清真指南》一書。
馬注看到清朝的西進運動使得“西學”東漸甚至“經教漸開”。尤其在“華”“西”一體之際,皇帝如此“詢道窮理”,馬注感覺大清的大一統“未必非清真之幸業”。在其《進經疏》中,馬注表達了對清朝保護回民的感恩之情, 并且陳述了了解清真的重要意義:“華西一體,痛癢相憐”。也就是說,馬注早已覺察到清代的西進運動需要朝廷更好地了解回教知識。正如李普曼(Jonathan Lipman)和張廣達所言,馬注的著述并不是對阿拉伯語或波斯語文獻的翻譯,而是在儒家背景下對伊斯蘭教的創造性闡釋。其宗旨是為清朝的大一統政治格局提供或補充有關伊斯蘭的知識。
如果說17世紀的回民知識分子通過哲學、詞義學、詞源學等方式間接委婉地應對部分內地士紳對回教的誣蔑,那么18世紀回民知識分子則直言不諱地將“回教”清真化歸咎于漢人士紳的偏見和攻擊。孫可庵在1720年著有《清真教考》一書。根據已有的漢文史料,孫在此書中呈現了一個從中亞到東南亞再到中東的穆斯林世界。在論述有關伊斯蘭教在中國時,他匯集了明朝的圣諭、元明的回回先賢以及御賜清真寺等種種政治關聯。他甚至將穆罕默德描述成如同孔子一樣的“圣人”。
當時就任于翰林院四譯館的金天柱對陳世倌、魯國華、岳鐘琪等人的反回奏折耳熟能詳。他的《清真釋疑》就是對這些反回士紳的回擊。在自序里,他闡明了著述此書的緣由:
清真者,吾教之宗,釋疑何為而作也?由于各教莫能思吾教之行事,蓄疑團于千百年而莫釋,未學吾教之書而不知其所以然之故,致使各教之疑愈生而各教之物議愈紛。遂有謂不遵正塑,私造憲書,以三百六十日為一年而群相慶賀者;有謂異言異服,揀擇飲食;甚者謂齋仍茹葷,白日何故不飲食?又謂禮拜不知所拜何神而夜聚曉散,男女雜沓;更謂齊發以毀父母之遺體,而龐貌為之異樣者。種種疑案皆莫能釋。
金天柱開宗明義地指出了撰寫《清真釋疑》的緣由。他在自序中列舉了種種誣蔑如陳世倌、魯國華等漢人士紳的奏折。金天柱甚至使用了“疑案”一詞,表明這些誣蔑事件已經被立案審查。根據金天柱的說法,以往對伊斯蘭教沒有闡釋,“非吾教之無人”,而是“蓋緣吾教諸前輩只自作大言而不屑白此目前疑案”。而他的釋疑之說“亦迫于各教之橫議而起者”。為此,他“為略抒鄙言,俾各教之人思其理之合一,事之大同,疑心頓釋,而吾教之道庶不無小補云爾”。也就是說,金天柱注釋的行為實際上是被迫而為,直接因素即“橫議”。
這些“橫議”之人就是上述反回之陳世倌、魯國華等人。換言之,金天柱的著述更多的是對回教的儒教式回應和正名。正如馬廷輔在序中指出的那樣,其著述之參考資料基本是內地儒釋道,其文風和筆調幾如韓(愈)、柳(宗元)、歐(陽修)和蘇(軾)。
正是在這種政治、社會、文化背景下,清代回民知識分子不僅以文學的形式回擊部分士紳的誣陷和攻擊,更是構筑了一部回回愛國史。如成書于18世紀初期的《回回原來》,就將伊斯蘭的入華和唐王的邀請相聯系。馬注更是在清朝急劇擴張到中亞之際,不失時機地以其族譜勾勒出一幅回回與內地共命運的歷史圖畫。根據馬注的說法,其來自布哈拉(補哈喇,Bukhara)的先祖所非爾,早在宋朝神宗年間入華傳道;其后人蘇祖沙大約在1191年出使金朝并且“卒以殉難”;他們在布哈拉的后裔瞻思丁亦參與“會元滅金”。自此,回回廣布內地。馬注甚至希望清朝延續明朝褒獎回回圣人的做法,“招修天下清真,褒以封號”。為此,他“謹將歷代褒封欽嘉實據繕呈預覽”,希望朝廷“詳查往例”。
清代回民知識分子清楚地意識到,清代再次問鼎西北乃至中亞穆斯林地區的事實勾起了部分士紳對歷史邊疆族群如回紇的回憶和想象。通過對“回”的厘清和正名,他們試圖以“清真教”代替回教來切斷士紳眼中的回民和回紇關系。這一時期回民先賢的漢語著述“漢克塔布”主要是為了解釋和論證作為回民宗教的“清真教”和作為漢民信條的“儒教”之間的兼容性和共通性,所以在這個意義上來說,“漢克塔布”應該是“民克塔布”,即回民(而不僅僅是漢民)的宗教、文化也是更大的內地臣民群體——民——文化的一部分。正名是為了行事,這在清代甚至當代對“伊斯蘭”的不斷“正名”中體現得淋漓盡致。從17、18世紀將“回教”正名為“清真”再到20世紀中葉改為“伊斯蘭教”,它揭示出在變動的政治環境下回民、漢民以及國家之間不斷變遷的關系模式。當中國社會的基本政治、社會和族群面貌發生巨變時,諸如“族”、“教”、“民”等基本概念也隨之被重新質疑和定義。
結語
縱觀元明清史,也許人們會問,穆斯林在19世紀末之前的元、明、清不但與統治階級相安無事,甚至為各朝的締造和宏業作出了巨大貢獻。如元代的穆斯林商人、官員、工匠、軍士和明代的下西洋、出使西域,都少不了回回人的身影。甚至滿人的亞洲內陸盟友也囊括了回部、蒙古、藩部等地。無論是承德的回文碑刻還是北京的回部上層聚居點都反映出滿人和穆斯林的友好關系。在大一統的多民族大清(Daicinggurun)帝國境內,為何漢人士紳和回回學者的文字交鋒超越了宗教和文化的正常哲學探討而驚動了朝廷。
自17世紀到18世紀中葉為止,清朝疆域空前擴大,臣民人口急劇增加,政治、社會、文化生態空前變遷。首先,清代大一統的政治局面和“懷柔遠人”的民族政策使得“歸降” 和“內附”的藩部人口急劇增多。這不但引起了諸如馬注這樣的回民學者的關注,同樣也引起了諸如魏塾這樣的儒生的文化攻擊甚至排外。尤其在清代的“文字獄”背景下,士紳官員不敢直接攻擊異族滿人朝廷,只好指桑罵槐地變相攻擊內地回民和回教。如同其他亞歐帝國諸如奧斯曼出于維護帝國利益的需要而保護基督徒和猶太人,莫臥兒保護印度教一樣,大清對國境內不同臣民間的文化攻擊和族群歧視一直保持著高度的警惕。尤其在內地,正如康熙、雍正以及乾隆所指出的那樣,朝廷不“異視”臣民,無論是“漢民”還是“回民”。這里我們看到的是一個真正的“多元一體”的“族-民”政策,即無論什么“族”都是“民”的一部分。
?????????????????????????????????? (作者單位:美國霜堡州立大學歷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