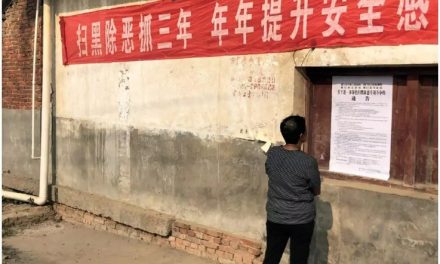陳柏峰
人情是中國民間的一種普遍習俗,它有著重要的社會功能。在經濟層面上看,它是一種互助機制,人們可以依靠它轉移因生命周期變化而來的辦大事的壓力;在社會整合層面,它是一種維護社會團結的機制。然而,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人情尤其是儀式性人情發生了很大異化。在某些地區,儀式性人情場合的送禮數額非常高,招待客人的酒席標準也很高,這導致處于村莊底層的村民根本操辦不起儀式性人情,也就無法廣泛參與。這樣,儀式性人情的規模大小就與村民在經濟分層中的位置相吻合,儀式性人情場合最終變成了經濟分層的社會確認場合。
不同階層農戶在儀式性人情場合的表現
筆者在寧波鄉村調查中聽村民們講,送禮金額的增加主要是1990年代以后加速的,在其后的十多年間,禮金數額增加了十多倍。其中,來自朋友的禮金及其數額都快速增長。禮金數額的增長,當然與村莊經濟的發展相關。村莊經濟的發展為儀式性人情場合禮金數額的增長提供了可能,但禮金數額的增長速度卻超過了村莊經濟的發展速度。比如說筆者調查中的蔣村村民人均年收入1994年是1000元左右,2007年這一數字上漲到7000元左右,僅增長了7倍;而同一時期,人情禮金卻增長了10倍左右。但這還不是問題的關鍵。問題的關鍵在于,村莊經濟的發展造就了農戶經濟的分化,村里出現了少量富裕階層農戶、一批小康階層農戶、大量的中間階層農戶和個別相對困難農戶。一個富裕階層農戶的年收入比30個中間階層農戶的總收入還要多,而中間階層農戶和困難農戶的收入增長遠遠跟不上人情金額標準的增長。在這種情況下,中間階層和困難戶該如何面對儀式性人情的壓力呢?富裕階層在儀式性人情中又是如何表現的呢?
不同階層的農民在儀式性人情場合的表現和作為是不相同的。儀式性人情場合的來往是互惠的,因此從長期來看是平衡的。當別人“辦事”時,與之保持社會關系的村民前去送人情;當村民自己“辦事”時,他的社會關系范圍內的村民都會來“回人情”。當客人來“送人情”時,辦事的人家需要用酒席招待來客。過去,酒席比日常生活中的伙食稍好一些就行了,其成本花費會遠遠低于客人的人情金額。這樣,人情的經濟互助功能就體現出來了。而現在,所收的“人情”金額與招待客人的酒席成本差不多,甚至不抵成本。因此,盡管人情在來往上仍然是平衡的,但每一次儀式性人情場合卻變成了一次集體揮霍和浪費。富裕階層和小康階層當然有資金、有能力去浪費,因為浪費的錢財對他們來說不算什么,而同樣的錢財對于中間階層和貧弱階層則是一筆巨大的開支。中間階層中的多數村民在強大的輿論壓力下,也只能“踮起腳來做人”,不得不浪費錢財——當然,他們會盡量少浪費一點。貧弱階層農戶面臨強大的壓力,如果實在沒錢,浪費不起,也只好作罷。
中間階層農戶為了盡量少浪費錢財,可以有兩種辦法:一是降低酒席標準,讓儀式性人情像過去一樣有錢結余;二是自己盡量少舉辦儀式性人情,即使舉辦也盡量少邀請村民,同時盡量少參加其他村民舉辦的儀式性人情場合。但是,在強大的輿論壓力下,第一種做法顯然不太可行,因為這樣會被村民指責“辦不起就不要辦”。因此,村莊中下階層一般采取第二種方式,即不在萬不得已的時候不舉辦儀式性人情。即使操辦,村莊中下階層農戶請的客人也比富裕階層和小康階層少得多。
與中間階層和貧弱階層的農戶盡量壓縮人情交往不同,富裕階層和小康階層的農戶則顯得非常自由,他們不需要擔心錢財問題,不需要謹慎小心。他們有錢,可以廣泛參與各種人舉辦的儀式性人情場合,可以借此建立或保持各種需要的社會關系。當他們自己舉辦儀式性人情時,場面更重要,而錢財顯然不是問題。親戚、朋友、莊鄰只要出現在他們的儀式性人情場合,他們就很高興,覺得很有面子,而人情禮金真的無所謂。但關鍵是,貧窮的親戚、朋友和莊鄰,如果拿不出人情錢,他們是不會出現在酒席中的。即使主家不介意,村民輿論也很難寬容他,他們自己也無法坦然。
顯然,在儀式性人情的舞臺上,富裕階層和小康階層可以表現自如;而中間階層和貧弱階層則在高漲的人情和酒席標準面前捉襟見肘。他們必須精打細算、謹慎小心,才能在硬性的人情和酒席標準與有限的經濟收入之間保持平衡。
經濟分層的社會確認和階層排斥
通過儀式性人情場合,富裕階層和小康階層可以有越來越多的朋友、莊鄰和親戚,而中間階層和貧弱階層卻只能將自己的朋友、莊鄰和親戚限制在一個狹小的范圍之內,甚至不得不放棄與很多朋友、莊鄰和親戚的人情交往;最貧窮的人則喪失了人情交往的資格,在人生的重要時刻,甚至不再有舉行慶祝的資格,也不再有通過人情獲得幫助的可能性。人情已經喪失了其經濟互助功能和社會團結的維護功能。相反,它日益成為村莊經濟分化的社會階層確認場合和方式。一個農戶在村莊中的經濟位置,通過儀式性人情場合就能輕易看出來;反之,一個農戶在村莊中的經濟位置和狀況,決定了他的人情交往范圍和社會關系范圍。
儀式性人情的本來意義并不是大操大辦,其真正目的在于通過辦事增進社會團結,促進互相幫助。從理論上說,貧窮的農戶也有貧窮的親戚朋友,遇到大事時可以互相幫助,窮人的大事也可以窮辦。既然大家都貧窮,辦事時就可以多講一些實惠,少講一些排場,從而集中力量辦大事;在儀式性人情場合,大家可以少送一點禮金,可以不吃那么多山珍海味,不那么鋪張浪費,可以將人情禮金節省出來辦事;也可以聚在一起好好交流,增進互相了解和聯系紐帶,增進社會資本和社會團結。然而,目前的人情規則堅持的并不是這種邏輯。在現在的村莊語境中,“窮人辦窮事”沒有任何合法性,村莊輿論堅決維護禮金數額和酒席規格的高標準,其核心是“你辦不起就不要辦”。顯然,這種對儀式性人情的普遍認識是不利于中下層貧窮農民的。
中下層貧窮農民越來越成為說不起話、做不起人的觀眾,他們只能看村莊富裕階層和小康階層農戶在儀式性人情場合的表演。他們很少能夠參與其中,偶爾參與也是謹慎小心。儀式性人情越來越成為村莊上層農戶排斥底層農戶的一種工具和手段。借用這種工具和手段,他們可以展開越來越廣泛的人際交往,可以動員和利用各種社會關系,可以在社會交往層面和村莊公共舞臺上將貧弱農民徹底邊緣化。這種邊緣化很快會上升到貧弱農民的心理層面,讓他們自感做不起人,是低人一等的人,因此越發放不開,甚至行為動作都會給人笨拙的感覺。從而,這最終會從心理和事實上強化富裕階層和小康階層農民的優越感和優勢地位。因此,當前農村儀式性人情不但是經濟分化的社會確認手段,還是優勢階層對中下階層農戶實行社會排斥的工具。在這其中流行的是一套對富人有利的話語,這種話語被廣泛接受,也正反映了富裕階層和小康階層農民在村莊中占據著文化支配地位。
吊詭的是,儀式性人情雖然具有社會階層的確認和排斥功能,但它在人情的進入和退出機制中卻貫徹了意志自由原則。這種機制借用了儀式性人情的禮儀。在農村儀式性人情場合,一般需要辦事的主家向客人發出邀請,俗稱“請”,這種“請”是民俗禮儀的一部分,本來不含控制權,但在當前情境下越來越含有控制權的含義。比如在我調研的蔣村,請客是自由的,請誰不請誰,是主家可以自由把握的。在一些儀式性人情場合(如結婚、小孩滿月),如果主家想請客人,就會事前向客人送糖果,否則就不送,親戚、朋友、莊鄰以是否收到糖果作為是否受到邀請的標志。沒有收到糖果的村民,如果想主動與主家“建交”,也可以先送雞蛋過去,這構成了一個“要約邀請”,主家如果接受這種“建交”示意,就會再送糖果過來。在另一些儀式性人情場合(如喪事),辦事的主家以放鞭炮為信號,鞭炮一放,村里人都知道他家要舉辦儀式性人情,可以自由選擇是否參與其中。如果主家并不想與前去的某一農戶結交,他會在事后退還人情禮金。常常有富裕的農戶考慮到貧窮農戶的經濟狀況,而主動退還人情禮金的,這通常會讓貧窮農戶非常感激。
看起來無論富裕農戶還是貧窮農戶,在人情交往中都是自由的,他們在別人辦事時可以自由選擇是否參與,也可以在自己辦事時自由選擇參與的客人。正是這種進入和退出機制的微觀層面的主動性,才讓貧窮的農戶有一個臺階可下,否則他們的家庭經濟將被儀式性人情徹底拖垮。但是,這種自由選擇現在卻是建立在農戶家庭經濟狀況的基礎上,只有富裕的農戶才能將儀式性人情場合辦大,才能廣泛參與儀式性人情;在當前村莊文化的情境下,縮減儀式性人情規模、退出人情交往意味著默認自己的經濟狀況不行,默認自己處于社會階層的低端。最終的結果必然是富裕階層就掌握了村莊的文化主導權。
在儀式性人情的互動場合,農戶在選擇行為時的意志表達是自由的,采取的行動也是自由的。只是這種自由是非常有限的,這是在既定社會結構下的自由,是在不利于貧弱階層的文化支配下的自由;恰恰正是這種微觀的自由選擇在宏觀上最終導致了階層排斥。也就是說,儀式性人情的社會階層確認和排斥機制有著一套精微的制度安排。在這種制度安排下,貧弱農戶的自由選擇最終確認了階層排斥。
儀式性人情的功能異化及其原因
費孝通曾在《鄉土中國》中講道:“在傳統結構中,每一家以自己的地位作中心,周圍畫出一個圈子,這個圈子是‘街坊’。有喜事要請酒,生了孩子要送紅蛋,有喪事要出來助殮,抬棺材,是生活上的互助機構。可是這不是一個固定的團體,而是一個范圍。范圍的大小也要依著中心的勢力厚薄而定。有勢力的人家的街坊遍及全村,窮苦人家的街坊只是比鄰的兩三家。”費孝通在寫作《鄉土中國》時僅在江南和云南有實地調研經驗,這段寫作也許是以江南的市鎮作為經驗基礎的,而江南市鎮那時已經逐漸與理想狀態的傳統農村社會有所不同。在費孝通生活的時代,江南的商品經濟已經比較發達,村莊經濟分化已經起步,因此他既看到了儀式性人情的傳統互助功能,也看到了儀式性人情異化為階層排斥的一面。其實,在傳統農村社會,貧窮或富裕確實會影響家庭人情圈的大小,但這種影響并不是絕對的。一般情況下,人情圈是有一個基礎性范圍的,人們不會僅僅因為貧窮而遭到排斥。
當然,這并不是說傳統農村社會的人情圈不存在社會排斥。在傳統村莊社會中,這種社會排斥主要不是經濟上的(雖然不能否認村民有趨炎附勢的傾向),而是一種基于道德評價的排斥。村莊道德的越軌者常常會被排斥在人情圈之外。人們在儀式性人情和非儀式性人情場合遠離道德越軌者。那些道德有瑕疵的村民,由于人情關系往來少,逐漸就成了嚴重缺乏社會關系的“死門子”。正是通過這種道德排斥,村莊地方性規范得以維護,儀式性人情維護村莊社會團結的功能得以凸顯。
顯然,從道德排斥向階層排斥的發展,是儀式性人情功能異化的表現。這種異化固然與村莊經濟分層有關,但也有其村莊的內生原因。其中最重要的一點是,寧波農村并不存在強大的內生結構性力量。在我們調研過的其他一些村莊(如鄂東南農村),村莊中存在強大的結構性力量,宗族之下的房份仍然有號召力,因此在這些地方雖然也發生了較大的經濟分化,但儀式性人情并沒有異化為經濟分層確認和階層排斥的手段。
在存在結構性力量的村莊中,每個人的位置是確定的,需要遵循尊卑長幼的秩序。在儀式性人情場合,該請的客人、該送的禮金都是較為確定的,并非個人可以自由選擇。其中,個人之間關系的展示、感情的表達需要通過人情,但必須受到結構性力量的制約。因此,特定身份的人情禮金,不能根據個人的喜好來確定,而必須遵循村莊中特定身份應該用多少禮金來表達的地方性規范。違反這種地方性規范,就會遭到人們譴責,甚至遭到嘲弄和奚落。很多地方農村也因此流傳著一些情節類似的故事:兩個身份相同的親戚去參加儀式性人情場合,一個富有一個貧窮,富有的親戚為了顯示自己富有,送禮時出手很闊綽,將貧窮的親戚比得很難堪;大家為此都頗為不滿,于是合謀臨時增添了一項送禮項目,結果富有的親戚由于之前送禮已將錢花完而更為難堪。這種故事多是告訴人們,儀式性人情場合的送禮金額并不能隨心所欲,而應當遵循普遍認可的標準。在這些村莊中,酒席的規模和質量不僅代表單個家庭,還代表整個房份或小親族的名譽,當然也是操辦得越好越能受到贊譽,而這種操辦往往也處在房份或小親族的主導之下。正因此,房份或小親族的主事者也會考慮主事者家庭的經濟承受能力,酒席也就不會辦成沒有原則的“夸富宴”。
顯然,在有內生結構性力量存在的村莊中,儀式性人情場合的禮金金額和酒席標準不會毫無原則地飛漲,進而最終將貧弱農戶排斥在操辦能力之外。而在寧波農村,村莊中幾乎不存在任何內生的結構性力量,村民之間關系高度原子化,個體農戶辦事時,宴請的客人、送禮的金額等都可以自由選擇。他們可以完全根據個人情感好惡來決定一切,決定是否請某一位客人,決定是否與一位遠親繼續保持人情關系,決定具體禮金該送多少。所有這些都是個人的自由意志所決定的,僅僅受到自身經濟能力的限制,并不受來自外界的任何約束。這樣一來,自由的制度安排僅僅對村莊富裕階層和小康階層有利,而對村莊貧弱農戶非常不利。貧窮的農戶被迫在“自由”的名義下參與自己并沒有經濟能力參與的儀式性人情活動中。他們當然也有選擇退出的自由,但退出則意味著承認自己能力有限,承認自己處于村莊底層。貧窮的農戶在其中苦苦掙扎,而最貧弱的農戶也只能“自由”地選擇退出。于是,儀式性人情就異化成了經濟分層的社會確認工具和階層排斥的手段。
儀式性人情的異化其實是當前鄉村社會劇烈變遷時期發生的一種名義與實質相分離的現象。“名實分離”是社會轉型時期的普遍現象。費孝通曾指出,在一個變動緩慢的社會結構里,傳統的形式是不準反對的,但是只要表面上承認這形式,內容卻可以經注釋而改變。對不能反對而又不切實用的教條或命令可以加以“歪曲”,只留下一個“面子”。這么做難免不口是心非,滋生虛偽和歪曲,但這不可避免。名實之間的距離會隨著社會變遷的速率而加大。當社會加速變動時,注釋式歪曲原意的辦法無法避免,因此位與權,名與實,言與行,話與事,理論與現實,會全趨向于分離。人情異化中的“名實分離”,與費孝通所說的還不完全一回事。人情異化中的“名實分離”并不是不準反對傳統的形式,而是在儀式性人情中新出現的各種事物和現象,只是借用了傳統事物的形式,從而使得儀式性人情的表面與內核、形式與實質發生了分離。在變化很慢的傳統社會中,占統治地位的村莊長老權力不會容忍這種分離;而當前社會發生的劇烈變遷,使得人情的表面與內核、形式與實質都發生了根本的分離。
(作者單位: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法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