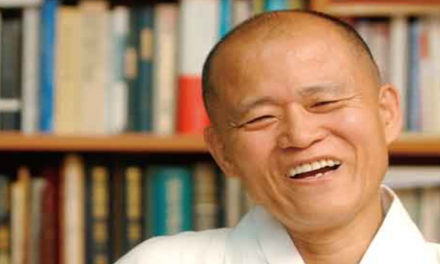黃萬盛
[文章導讀]21世紀以來,中國的迅速崛起深刻改變了全球政治經(jīng)濟結(jié)構(gòu),隨著此一進程的深化,重新確立中國文化主體性的問題日益突出、亟待解決。然而,盡管今日中國傳統(tǒng)文化呈現(xiàn)出全面復興的態(tài)勢,但其往往以一種整全性的、模糊的面貌呈現(xiàn)于世,“傳統(tǒng)”愈發(fā)成為一個空泛的詞匯。本文作者從軸心文明比較的視野出發(fā),指出其他軸心文明都是由外在超越的權(quán)威性存在主導凡俗世界,是二元論的世界,而中國文明最深刻的意義卻潛藏于凡俗社會,這一凡俗人文主義給個人能力和精神以無限發(fā)展的空間,由此為中國傳統(tǒng)的復興提供了一個可能的切入點。
價值問題的強勢回歸
當中國經(jīng)濟突飛猛進、取得人類歷史從未有過的奇跡時,有人把中國看作一個經(jīng)濟動物;當這種經(jīng)濟奇跡與政黨政治、憲政民主幾無關(guān)系時,又有人把中國看成是政治怪物。即使像蘇珊· 桑塔(Susan Sontag)那樣對資本主義的弊病有深刻洞見的優(yōu)秀思想家,談到中國時也頓感茫然,她說“中國是物件,是不存在”。故宮、長城是物件,但這背后的精神世界是什么呢?有多少人能夠說明白呢?即便是炎黃子孫又何嘗不是陌生地面對自己的祖國?中國是什么?在那無窮無盡的現(xiàn)象背后,什么是中國的本質(zhì)?這一問題與民族的價值體系、認同感、主體性緊密相關(guān)。
價值問題目前在國際思想界、文化界和學術(shù)界占據(jù)了突出的地位,其一度被視作相對的,所以不能用真理的方法予以討論。因此,在美國的很多大學中,連倫理學和美學的課程都開不出來,因為其缺乏一個恒定的評價標準,沒有確定的意義。在過去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nèi),語言哲學、邏輯哲學、分析哲學,主導了大學的哲學教育,以至于哈佛大學中一度沒有教授能夠講授倫理學,校方不得不從普林斯頓大學請教授來幫助上這門課程。但在最近二三十年的社會思想和學術(shù)研究領(lǐng)域中,價值問題呈現(xiàn)出強勢回歸的態(tài)勢,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在于,當探索物質(zhì)現(xiàn)代化背后的隱藏機制時,所謂現(xiàn)代性問題就浮出了水面,即具有哪些品質(zhì)才能被稱為現(xiàn)代化?這就把價值體系的問題帶了出來。在蘇聯(lián)解體、東歐劇變之后,美國認為自己所代表的核心價值具有普世的意義,所以才能征服蘇聯(lián)、東歐的人心,引起社會的巨變。因此美國政府將進一步向世界推廣美國價值作為重要的戰(zhàn)略任務(wù),學術(shù)界開始重新關(guān)注價值問題。比較典型的就是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歷史終結(jié)論”,他認為長達一個世紀的關(guān)于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制度孰優(yōu)孰劣的爭論已經(jīng)可以蓋棺定論,歷史終結(jié)在了以美國為代表的資本主義體系中。
但與此同時,人們又看到在最近二三十年的美國社會中,無論是社會組織體系,還是經(jīng)濟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都不斷爆發(fā)出重大問題,且都產(chǎn)生世界性影響。特別是2007?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幾乎把整個世界都攪入美國金融衍生品帶來的災難之中。所以,美國學術(shù)界也有一批學者認為價值問題的探索遠未結(jié)束。舉個例子,哈佛大學的教授塞繆爾·亨廷頓(Samuel P.Huntington)認為,20世紀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對抗掩蓋了文明體系間的矛盾。冷戰(zhàn)結(jié)束以后,大文明之間價值體系的沖突,如今才剛剛登上歷史舞臺。亨廷頓在哈佛開了一門課,叫“戰(zhàn)爭地圖”(Wars map),他統(tǒng)計了從古希臘伯羅奔尼撒戰(zhàn)爭開始的每一場重大戰(zhàn)役,并用圖釘在地圖上將這些戰(zhàn)役的爆發(fā)地點標注出來。所有這些圖釘最終連成兩條線:一條是從南到北的線,這條線正好是基督教文明與其他世界文明的分界線;另一條是從東向西的線,其正好是儒家文明與其他文明的分界線。在此基礎(chǔ)上,亨廷頓完成了《文明沖突論》。這本書出版以后,經(jīng)過了一段時間,突然在美國社會引起很大轟動,遠遠超出了學術(shù)范疇。究其原因在于,“9·11”事件佐證了亨廷頓的觀點,文明、價值和信仰的沖突開始登上歷史舞臺。
亨廷頓為此非常得意,接受各種各樣的采訪,宣揚他的文明沖突論。但其后有一次事件讓亨廷頓比較窘困,因為“9·11”以后,美國決定出兵阿富汗,在戰(zhàn)爭中抓獲了一些塔利班士兵,發(fā)現(xiàn)在每個塔利班士兵的背囊中,都有一本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美國人覺得很奇怪,就問他們?yōu)槭裁磿l(fā)這本書?他們說這是塔利班的教戰(zhàn)書,既然美國人這樣看待伊斯蘭文明,他們?nèi)绻慌c美國抗爭,該怎么生存下去呢?當然,我們不能把恐怖主義的興起歸咎于亨廷頓及其著作。然而,如何認識人類各種文明,如何處理不同文明迥異的價值體系,毫無疑問已經(jīng)成為當代世界的主要課題。不同價值體系間是互相傲慢排斥、頤指氣使,還是相互尊重、相互學習?這已經(jīng)成為重要的世界安全戰(zhàn)略問題。
在最近的二三十年當中,由信仰、文明的地方性和精神性建設(shè)的問題,引申出一個最重要的課題——什么是核心價值?今日中國也碰到同樣的問題。從90年代,我在哈佛就處理過所謂“自由主義”和“左派”的課題,我稱其為“跨世紀的不對話的爭論”,自由主義和左派的爭論其實早已不是學術(shù)辯論,而是信仰、立場的對立,其核心就是我們應(yīng)當怎么處理“普世價值”的問題。此外,在中國現(xiàn)代化發(fā)展和成長的過程中,如何建立和發(fā)展中國本土的價值體系?無論經(jīng)濟增長多么迅速,歸根結(jié)蒂,中國現(xiàn)代化具有怎樣的典范意義?所有這一切問題,都要回到價值體系這一關(guān)節(jié)點上。
正因如此,過去十幾年以來,我最經(jīng)常提的問題就是,什么是中國崛起的文化意義?祖國越強大就越應(yīng)當問這樣的問題。今日中國已然成為一個龐大的經(jīng)濟體,外人很容易理解其經(jīng)濟方面的成就,以至于國外有學者把中國僅僅視作一個巨大的經(jīng)濟驅(qū)動的國家,海外的中國游客瘋狂地消費奢侈品,投資海外的中國人罔顧環(huán)境和當?shù)氐呢毨В挥J覦別人的礦產(chǎn)資源,除此以外,中國究竟給世界帶去了什么樣的文化消息、價值理念和思想體系?資本主義的發(fā)展耗費了150年左右的時間,把啟蒙運動所提出的自由、平等、博愛和現(xiàn)代生活方式、經(jīng)濟體系結(jié)合起來,取得了世界性的文化影響。自由、民主、平等,如今也都被寫入中國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中,在這方面,我們不應(yīng)自欺欺人,西方社會的確有成功經(jīng)驗值得中國借鑒,這些來源于西方的地方經(jīng)驗,經(jīng)過人類的實踐獲得了普世意義,依照同樣的邏輯,來源于中國的地方經(jīng)驗中,有哪些可以成為人類的普世價值呢?我們現(xiàn)在除了談西方的價值之外,對源于中國自身的價值的認同和發(fā)掘,還遠遠不夠,特別是在年輕一代中。現(xiàn)在的年輕人在談話的時候,使用的詞匯大多源于西方話語體系,其中源于中國自身的東西相當薄弱,這也是當前中國所面對的重要困難和挑戰(zhàn)。
主體性、身份認同與價值傳播
在價值的發(fā)掘與傳播中存在一個關(guān)鍵問題,即主體性(Subjectivity)的問題。如果社會主體缺乏開發(fā)、傳播本土價值的責任意識,那么即便是再好的價值也會流失掉。所以很多大的文明在歷史上曾經(jīng)作過貢獻,但是隨著歷史的演進,它的主體性被各種因素消解,或是殖民主義,或是經(jīng)濟浪潮,最后這些文明從人類歷史的舞臺上消失,成為一個歷史記憶,無法再次引導人類社會發(fā)展,兩河流域文明、古埃及文明都有這樣的經(jīng)驗教訓。從學術(shù)研究的角度來說,隱藏在價值體系背后的一個核心問題正是主體性。
我對主體性重要性的認識,主要是得益于哈佛大學教授艾瑞克· 艾瑞克森(Erik Erikson),他是美國社會心理學方面最重要的學者,馬丁· 路德是其幾乎一生的研究對象。他的代表作《青年路德》,在西方學術(shù)界有很大的影響。艾瑞克森仔細研究馬丁· 路德的日記、其同學的回憶、其所在社區(qū)的牧師與他的談話記錄,發(fā)現(xiàn)青少年時期的路德處在極大的焦慮中,惶惶不可終日。他一直在問一個問題:Who am I(我是誰)?在家里面,家長告訴自己應(yīng)該干什么;到了學校,老師告訴自己應(yīng)該干什么;到了社會上,神父告訴自己應(yīng)該干什么,一個人所做的任何事情都是別人告訴自己應(yīng)該干的。既然如此,上帝為什么還要把“我”放到這個世界上呢?“我”有意義嗎?“我”到底是誰?有沒有“我”自己應(yīng)該去干的事情?經(jīng)過長期的煎熬和辨難,馬丁· 路德完成了一個重要的思想蛻變:人可以不經(jīng)過教會而直接與上帝對話。此后他用畢生精力展開了一場破除教會對個人控制的運動,通過“新教改革”,把每個信徒個人的積極性作為社會真正的動力和源泉,在宗教內(nèi)部完成了人文主義的轉(zhuǎn)向。
當然,艾瑞克森所突出的馬丁· 路德的“who am I”命題中,也存在可以反思的問題,這完全是從自己的立場出發(fā)去提問,可是在英文中還有另一個角度,叫What is me(我是什么)?這一表述有著完全不同的含義,是從別人的立場來看自己,更多考慮別人的立場、感受。只有自己的立場而缺乏他人的角度,個人的解放最終就會變成自我中心論、徹底的個人主義。近代以來,西方意識形態(tài)的主要困境正在于無法擺脫個人主義的自我中心論,個人、社會、國家均是如此。美國的真正困難就是美國中心主義。這是“新教改革”的負面影響。即便是薩特(Jean-Paul Sartre)這樣的存在主義思想家也執(zhí)迷在“他人就是地獄”的狂熱中。而中國傳統(tǒng)基本是在“人己關(guān)系”中處理人的主體性,以他人為參照,發(fā)展自我意識,這樣的個人更少暴戾,更多關(guān)愛。今天來看,它的價值更高。
盡管如此,“新教改革”承擔了那個時代的任務(wù),把個人從教會的控制中解放了。過去我們認為宗教與人文是完全對立的,其實不然,新教把人文主義引到宗教領(lǐng)域中。這一思想后來深刻影響了以埃默森為代表的西方思想家,愛默生(Ralph Emerson)是哈佛神學院的教授,現(xiàn)在哈佛哲學系的大樓就被命名為“愛默生樓” (Emerson Hall),愛默生大力推動每一個教徒獨立與上帝對話,解構(gòu)教會對社會的控制,使每一個人都成為社會的主體精神和主體力量。
艾瑞克森的研究解決了現(xiàn)代學術(shù)的一個重要問題——身份認同(Identity)。每個人活在這個世界上,都有很多的認同問題。認同就是自我的根源性和自我的皈依所在,認同感構(gòu)成了個人的存在根據(jù),這就是主體意識。個人為什么會存在于這個世界上,因為有這些東西是其要付諸努力實現(xiàn)的,是其存在的責任。價值只有被認同,才會成為生命的精神動力,沒有認同和主體的價值,只是飄在云霧當中的話語和說辭。核心價值的重要方面就是它必須被廣泛認同,并是群體性的主體自覺意識,否則就沒有意義。
當代中國搞了很多價值條目,比如“五講四美三熱愛”等等,同時還動用國家機器去宣傳這些精神要素,可是這些精神要素的某些方面缺乏主體性,國人對其難以產(chǎn)生真切的認同感,所以它沒有辦法在實踐生活中充分展現(xiàn)出來。今天很多人對那個繁復無章的“核心價值”連說都說不清,怎么會發(fā)自內(nèi)心地認同此種價值呢?一個缺乏大眾認同的價值體系,不可能轉(zhuǎn)化為民族行為和民族精神。今天我們要建設(shè)中華民族的價值體系,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解決中國人的主體性和身份認同問題。
美國學界的中國觀
我在“費正清中心”做過一個專題講演,主題是《什么是中國?以及它的存在意義》。這當中有一個比較尖銳的問題:進入全球時代之后,中國人面臨一個主客體的認識關(guān)系問題,即怎樣去了解對方,如何通過了解對方來更好地了解自己。全球化提供了一個相互理解的巨大的舞臺。在早期階段,這個舞臺上流行一種誤解,即通過全球化可以建立標準化和統(tǒng)一化,進而把全球化變成了一個霸道的同質(zhì)化過程,尤其是超級霸權(quán)國家,總是習慣性地沉浸在這種迷幻中。事實上,全球化正好是一個多樣性的舞臺。正因為全球化的存在,不同國家、民族的精神文明才可以在這個全球舞臺上得到充分展示,進而獲得更大的獨立性、主體性和認同感。人類社會的發(fā)展才可能獲得更大的多樣和豐富的資源。
在全球化時代之前,人們的認識是建立在帝國主義時代的資本主義、殖民主義的基礎(chǔ)之上,從19世紀下半期到20世紀上半期,是資本主義大規(guī)模擴張的時代。這個擴張的時代引發(fā)了殖民和被殖民運動。以往中國學界強調(diào)殖民和被殖民是軍事和政治的占領(lǐng)行為,是經(jīng)濟上的掠奪和輸入的行為,時至今日,殖民更多被視作一個文化問題,也就是一個價值和精神的滲透和解構(gòu)的過程,很多原住民已經(jīng)找不到自己的精神家園,很多部落已經(jīng)失去自己的語言,他們的祭奠形式甚至是生活方式都已經(jīng)消失了,這都與殖民運動有關(guān),是殖民主義結(jié)果。
在19世紀的殖民主義運動中,印度是個非常重要的案例,可以引發(fā)很多反思。早期人類學其實是在殖民開拓的需要中應(yīng)運而生的,英國作為曾經(jīng)的殖民強國,其人類學家寫了很多研究印度的作品。到20世紀,隨著民族解放運動的發(fā)展和民族主權(quán)國家的不斷涌現(xiàn),早期殖民主義催生的人類學的弊端逐漸顯現(xiàn)。有一些人類學家、社會學家在看了英國人類學家關(guān)于印度的著作以后,親身到印度去生活,發(fā)現(xiàn)那些作品所述內(nèi)容與現(xiàn)實根本是兩回事——那是英國人眼中的印度,而不是印度人眼中的印度。因此,他們扎根到印度,試圖用印度人的眼光來重新看印度。在學術(shù)史上,開啟了人類學和社會學領(lǐng)域中去殖民化的新時代,在學術(shù)上把殖民主義文化影響清除出去。了解了這個前提,就可以知道我為什么要到費正清中心去講“什么叫中國及其存在意義”。我試圖針對美國社會看中國的那種殖民主義觀點,作出一個中國學者的回應(yīng),重建關(guān)于中國的本土認知。
先來看看早期美國學界對中國的認識,這里不得不提的便是美國現(xiàn)代漢學研究的代表人物費正清(John Fairbank)。費正清受到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很深的影響。在湯因比的觀念中,文明與文明之間的歷史交往就是“刺激和反應(yīng)”的過程:一個文明進入了另外一個文明,在軍事政治和經(jīng)濟文化方面,造成了各種刺激,被進入文明由此做出反應(yīng)。費正清深受此種觀念的影響,所以在他眼中,近代中國的歷史就是19世紀開始,西方列強進入中國,中國對西方做出回應(yīng)。這是很片面的觀點。但這個觀念深刻地影響了美國的漢學界和政界。美國漢學界有一些學者,以比較傲慢和狂妄的態(tài)度對待中國,就是因為在其觀念中中國只是一個反應(yīng)的存在,因此他們有責任去刺激中國。美國的政治家們也普遍堅持這種立場,認為他們有責任通過自己的刺激讓中國變得符合美國價值標準。問題在于,作為一個只有兩百年發(fā)展經(jīng)驗的國家,美國固然有很多創(chuàng)新心得,但其文化積累無論如何都是非常稀薄的,他們本應(yīng)當對中國五千年的文化財富保持虔誠的敬意,但現(xiàn)在卻帶有一種文化傲慢的態(tài)度。歷史哲學有一個基本常識,文化是絕對不會通過短時間暴發(fā)形成的,只有可以經(jīng)久傳承的生活方式才能產(chǎn)生恒久的文化。
費正清的學生柯文(Paul A. Cohen)也非常出名,他認為費正清的觀點有問題。中國作為一個大國,有如此悠久的歷史文明,怎么會沒有它自己的想法,完全隨著西方國家的刺激去反應(yīng)呢?他認為美國學者應(yīng)該積極主動地去了解中國,并提出一個口號——到中國發(fā)現(xiàn)中國。他認為西方社會之所以能夠走到今天現(xiàn)代化的規(guī)模,是因為其通過啟蒙運動重新發(fā)現(xiàn)了民主、自由、人權(quán)、憲政,假如在中國的內(nèi)部能夠找到不依賴西方而存在的這些觀念,就可以說明中國內(nèi)部也存在現(xiàn)代化的動力,而非單純的刺激–反應(yīng)了。立足于此,他在黃宗羲和其他一些人的著作當中找到了這些觀念。比如議員制度,在黃宗羲的著作當中已經(jīng)有了所謂“議郎”,按照人口的區(qū)域去選拔“議郎”,然后由“議郎”來討論社稷的安排。
日本學者溝口雄三也在做類似的工作,即重新建立“中國”觀念。但是我不滿意,什么原因呢?因為他試圖挖掘的都是西方的價值要素,假如在中國沒有發(fā)現(xiàn)西方的自由、憲政、平等觀念,是否意味著中國沒有自己的歷史呢?我認為他做的工作,與費正清沒有本質(zhì)區(qū)別,他們都是從西方的立場和觀念出發(fā)去理解中國。這些工作有沒有價值?有價值。從別人的眼中來看中國,可以發(fā)現(xiàn)多樣性視角,豐富國人對自身的認識。但這也有很大的負面影響,如果完全依賴他者的視角,就會消解中國自身的主體性,所以我們需要兩面地看,并不拒絕他們這些看法,這些看法對我們有價值,有些是我們疏漏的,導致了我們妄自菲薄。但是更重要的問題是我們?nèi)绾蝸砹私馕覀冏陨怼?/p>
美國漢學界另一位代表人物是列文森(Joseph R.Levenson),他是猶太教的信徒,這種身份使他對理解大文明的傳承有深刻的自覺。他認真通讀了儒家經(jīng)典,激動不已,認為這是人類文明的非凡成就。他對《圣經(jīng)》有非常好的研究,對西方宗教傳統(tǒng)有很深的理解。但他仍然對中華文明展現(xiàn)的文化規(guī)模,欣喜若狂,認為這是基督教、猶太教在很多方面沒有能夠照顧到的另一種偉大文明,中國古代文明有更好的涵蓋能力和包容性,有更深切的人文關(guān)懷。但是他很惋惜,認為這么好的文明如今卻不能繼續(xù)發(fā)展下去,因為儒家文明是為皇權(quán)政治服務(wù)的,它與皇權(quán)結(jié)合在一起。現(xiàn)在皇權(quán)已經(jīng)被打倒了,儒家的文明就喪失了存在的現(xiàn)實根據(jù),因此儒家是人類歷史上在20世紀看到的最令人悲傷的孤魂野鬼。這是列文森的中國觀念,在他看來,中國曾經(jīng)是一個偉大國家,但是現(xiàn)在談不上了。因為它的偉大思想沒有社會基礎(chǔ)去承接和落實。
其實,現(xiàn)在有新的學術(shù)研究可以解除列文森的這個困惑,法國的人類學家杜瑞樂(Joel Thoraval)帶領(lǐng)了一些日本的人類學家和英國的人類學家,在華南農(nóng)村做了幾年的田野調(diào)查,試圖解決一個課題:在華南農(nóng)村中沖突和糾紛的解決標準究竟是什么?他們采集了很多案例,比如村民和村長、婆婆和媳婦的糾紛解決案例,最后得出的結(jié)論是,解決沖突背后的價值標準和原則,幾乎全部是儒家倫理。由此可以肯定地說,儒家存活于中國的日常生活中,而這正是儒家的精神品質(zhì),也就是孔子所說的“道在日用倫常之中”。這個道不是懸在空中,而是與個人的日常行為、日常生活緊密相關(guān),其與帝國和王權(quán)解體與否沒有必然關(guān)系。如果列文森能夠活著看到杜瑞樂的研究成果,我相信他或許不會認為中國的思想文化只是一個文化荒原上的孤魂野鬼。
2007年我在巴黎做學術(shù)交流,杜瑞樂請我喝咖啡,就在薩特寫書的那個“鮮花咖啡館”。他問了我一個非常有趣的問題:1949年以后共產(chǎn)黨動用了強大的宣傳機器,建立了諸多行為規(guī)范和觀念,例如地富反壞右、階級斗爭等,其在杜瑞樂團隊的調(diào)查中幾乎沒有出現(xiàn),為什么?這是個很好的問題。共產(chǎn)黨花了那么大的力氣去宣傳新規(guī)范和價值,可是它們并沒有進入民眾的日常生活。在普通老百姓日常的各種調(diào)解活動中,反而是傳統(tǒng)儒家倫理在發(fā)揮主要影響。當時,因為他突然發(fā)問,我沒有深入思考,給了他一個非常膚淺的解釋:一個可能的原因是撇開階級斗爭、人與人之間你死我活這一套體系,共產(chǎn)黨所強調(diào)的其他很多行為范疇,與儒家思想并沒有本質(zhì)的沖突。而階級斗爭是一個非常特殊的政治行為準則,當政治生態(tài)改變后,它就沒有存在的基礎(chǔ)了。從根本上說,階級斗爭的行為規(guī)范與中國傳統(tǒng)生活方式中的核心價值格格不入,階級斗爭一定會摧毀儒家倫理,回歸儒家倫理肯定不能容納階級斗爭。因此即便是在最嚴酷的階級斗爭環(huán)境下,我們?nèi)匀荒芸吹饺饲闇嘏⑷诵年P(guān)愛。眾所周知,就日常生活而言,在1960年代以后,階級斗爭才成為顯著重要的問題。“以階級斗爭為綱”成為國家的基本立場,強勢滲入日常生活的一切領(lǐng)域,嚴重地破壞了社會基礎(chǔ),這是毋庸諱言的,也是我們需要反思和記取的沉重教訓。
正因為共產(chǎn)黨宣傳的很多道德原則、行為規(guī)范其實是根源于儒家的文化,二者并不背離,所以杜瑞樂的調(diào)查結(jié)果最后才是通過儒家道德的面目呈現(xiàn)的。西方社會,尤其是美國,在最近三四十年都以西方價值規(guī)范體系下的刺激–反應(yīng)來看中國,杜瑞樂的研究是對中國重要的再發(fā)現(xiàn),也解構(gòu)了僅僅從皇權(quán)體制了解中國的狹隘觀念。
什么是中國道路
把上述歷史背景梳理清楚了以后,我要問:什么是中國?什么是中國的主體性?這是一個極難解決的問題。李鴻章有過一句名言:中國正在經(jīng)歷“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借由洋務(wù)運動以后的一系列社會實踐,西方的技術(shù)、經(jīng)濟、觀念、學術(shù)乃至于政治規(guī)范,大規(guī)模地進入中國,使中國開始全面的重新自我定義。這也是當代社會學中的重要問題,英文叫self-definition。
這個歷史階段的時間跨度差不多超過一百年,中國是如何重新定義自我的呢?從洋務(wù)運動期間的學習西方器用,到戊戌變法時期的改革制度,再到五四運動時期的改造國民性,都只算開了個頭,自那以后,中國一直糾纏在能不能走進現(xiàn)代化的困境中,全盤西化失敗以后,“十月革命一聲炮響送來了馬列主義”,馬列主義與中國實踐的結(jié)合為中國提供了一條新的發(fā)展道路。然而,直到今天,我們?nèi)匀辉谔綄がF(xiàn)代化的道路,尤其是當期待已久的經(jīng)濟騰飛終于開始時,我們發(fā)現(xiàn)中國主體性的問題不僅沒有得到解決,反而更加撲朔迷離了。30年的現(xiàn)代化進程,使得自我定義的問題更加復雜。前段時間有機會和一位老領(lǐng)導聊天,他對市場經(jīng)濟要在中國發(fā)揮決定性作用的表述有想法,他不能接受。什么是中國要走的經(jīng)濟道路、社會道路和政治道路?這些都是重要問題,都屬于我們自我定義的問題范疇。
舉個例子,1920年代正是中國知識分子積極從西方引進思想大潮的時代。胡適把他在哥倫比亞大學讀書時的導師杜威(John Dewey),請到了中國。杜威是美國實用主義的代表人物,他在中國轉(zhuǎn)了一大圈,留下五大講演,出了一本書叫《杜威五大講演錄》。現(xiàn)在知道,杜威那次來中國,是出于美國當時的情報機構(gòu)交付給他的任務(wù),讓他在中國了解一下,未來中國會向哪里走?是走資本主義的道路?還是會走社會主義道路?杜威回去以后給情報部門寫了個報告,他認為,中國一定會走資本主義道路,沒有任何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可能。這封信過了美國機密解禁期,早些年中國也有學者翻譯了這個文獻。與杜威差不多同時期訪問中國的,還有英國哲學家羅素(Bertrand Russell)。他對未來中國的發(fā)展道路做了不同的預判,認為中國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可能性最大。二人都是了不起的哲學家,居然對中國的未來做出了完全相反的判斷。為什么?這本身就是研究當代中國非常有趣的課題。
我后來與國外的一些學者探討這個問題,他們用了一些經(jīng)驗主義的方式解釋這個問題,指出觀點的不同是和他們活動區(qū)域、旅行線路和觀察到的現(xiàn)象有關(guān)。杜威主要的演講區(qū)域是上海和廣州。當時上海和廣州的民族資本和買辦資本都比較活躍,杜威看到的是資本主義氣象,所以他認為中國會走資本主義道路,他在中國北方的時間太短。而羅素的主要活動在北京,他是給北大、燕京大學的學生講課,他獲得的地方經(jīng)驗不同于杜威,因此他們做出了不同的判斷。
然而,我覺得以上解釋太表面了,其實中國南方的社會主義思潮并不比北方少。更關(guān)鍵的問題恐怕還是他們各自的學術(shù)背景對“他者”的態(tài)度所決定的,是對中華文明理解的問題。杜威基本上是在德國受理性主義哲學的訓練,在美國發(fā)展實用主義,實用主義突出“有用就是真理”,往往以對自己是否有利作為考慮問題的基礎(chǔ),很容易發(fā)展出自我中心論。我懷疑假如沒有胡適這個學生鞍前馬后地鳴鑼開道,杜威會不會來中國都是問題,事實上,他那一代美國學者真正把中國當研究對象的寥寥無幾。而實用主義塑造的美國心態(tài)和美國視野即使在今天都比比皆是。羅素的學術(shù)活動主要在歐洲,當時歐洲的社會主義思潮已經(jīng)形成規(guī)模,資本主義發(fā)展的弊病使得歐洲困難重重、險象環(huán)生,加上羅素本人對社會主義有同情的理解,可能影響了他對中國的看法。我們需要學習西方的學術(shù)智慧,但是必須了解所有的學術(shù)都有自身背景的規(guī)定,有些甚至還有利益驅(qū)動,他們可以成為我們的參考,卻一定不是我們可以照搬直抄的教義。
我們今天這個時代遠遠比杜威、羅素那個時代要復雜,我們所面臨的問題也比費正清、柯文或者列文森復雜得多。當代中國在現(xiàn)實層面跨出的步伐根本不是他們所能想象的,世界的變化也遠遠超過了他們經(jīng)驗想象所及的范圍。大量的國際資本進入中國,中國制造遍布全世界,中國的生產(chǎn)力、經(jīng)濟規(guī)模深刻影響著世界經(jīng)濟格局。全世界都在疑惑地看著中國的崛起,中國貢獻、中國影響、中國威脅、中國崩潰,各種各樣的“中國”莫衷一是。因此,在這個條件下,我們更需要冷靜地問自己:中國是什么?什么是中國的身份?如果我們不能確立自己的主體性和身份認同,我們就不可能發(fā)展出中國崛起的文明意義和價值意義,也不可能發(fā)展中國的普世價值。
重建中華文明的主體性
我在國外生活了二十多年,最經(jīng)常被問到的問題是:中國沒有宗教,那么中國的國家和社會是靠什么維系的?而且還維系了這么長時間,真是不可思議。借用雅斯貝爾斯的軸心文明學說,我試圖為理解中國提供一個切入點。
雅斯貝爾斯(Karl Theodor Jaspers)提出的“軸心文明的爆發(fā)”,就是在公元前4世紀到5世紀交通條件幾乎不允許進行跨區(qū)域直接溝通的情況下,人類不約而同地出現(xiàn)了四大文明體系:希臘的文明、耶路撒冷的宗教文明、印度恒河的文明和黃河流域的中華文明。這是雅斯貝爾斯了不起的貢獻,但是他只做了大文明體系發(fā)生學的工作,還有更深入的工作沒能涉及,即研究文明屬性和品質(zhì)以及它們所影響的歷史軌跡,進而對這四個軸心文明做一個品質(zhì)和功能的比較,這是我們應(yīng)當做的工作。
希臘的文明是理性超越的文明。柏拉圖有個經(jīng)典說法,叫做“洞穴人”:理性的太陽高高在上,而人不過是洞穴里面的一片混沌,人只有從洞穴中出來,被理性的光芒照耀后,才能認識事物,看清事物的面目。所以,理性是外在的、客觀的,是世界的根據(jù)、文明的主宰。尋找理性、服從理性,是人的光明之路。凡俗的世界是一片霧霾,等待著理性太陽的光芒照耀,有說法認為柏拉圖代表的是客觀唯心主義,因為他所指的理性是在人間之外、懸在天上的,這是希臘文明非常重要的特點。到了近代,西方思想家認識到理性不是外部自在的,而是人的思想和認識的產(chǎn)物,理性之光不再是天上的太陽,而是人的智慧,理性主義從客觀轉(zhuǎn)到了主觀。這個突破引導了近代思想解放運動,有了了不起的貢獻,但也出了很大問題。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主張,回到前蘇格拉底時代,傾聽存在的聲音,就有鮮明的針對性:人把主觀理性當做至高無上的權(quán)威,不再尊重自然,不再相信情感,不把客觀當回事,這就是理性主義的傲慢和災難。
關(guān)于納粹集中營有過很多總結(jié),其直接指向了理性主義。納粹災難的背后,有理性傲慢的影子。“二戰(zhàn)”后的德國哲學界在這方面有些反思,有一個現(xiàn)代寓言:有一個人掉了鑰匙,鑰匙是很重要的東西,可以打開很多的門,結(jié)果他老在同一個地方找,老在一個小圈子里轉(zhuǎn),轉(zhuǎn)了幾十遍以后,他還在那里轉(zhuǎn)。有一個人過來問:“你老在那轉(zhuǎn)悠干嗎?”他說:“我的鑰匙丟了。”那個人說:“你已經(jīng)在這里找了幾十遍了,它總共就這一點地方,你已經(jīng)千轉(zhuǎn)百回還看不清嗎?”那個找鑰匙的人回答說:“我之所以在這里找,是因為這有光。”最后這句“因為這有光”意味深長,理性覺醒是啟蒙運動的主題,啟蒙的英文詞是enlightenment,也就是在光中、沐浴光明。找鑰匙的寓言非常具有諷刺意味,是針對光而言的。理性的光芒會造成理性的迷信,屏蔽掉很多的空間,對人的認識和能力的自以為是到了瘋狂的地步。那么光沒有照到的地方怎么辦?難道這些地方就沒有價值了嗎?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的思想為什么能夠有那么大的影響力,其思想最核心的原則是抗拒理性的傲慢。捷克的作家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說:“人們一思索,上帝就發(fā)笑。”也就是對迷戀理性思維能力的嘲笑。一個人自以為掌握了理性,可是卻經(jīng)常犯錯誤。美國當代哲學家羅森(Stanley Rosen)說的更直白:“啟蒙是挺好,只是光太亮了。”太強的光反而灼傷了人的雙眼,更看不清事物了,所以要對理性保持足夠的警惕,別被主觀主義、意志論引導到理性主義災難中。這是希臘理性文明存在的問題。
在耶路撒冷的宗教文明中,上帝是一個全能的主宰,世界是上帝造的。用了7天時間造了世間萬物,包括人類。它是一個二分的世界,上帝是一個全能的存在,而我們生活在一個凡俗的世界。凡俗的世界是有罪過的,人是有原罪的。人通過在凡俗世界中的贖罪和洗禮,才能重新回到上帝的懷抱。
在恒河流域的文明體系中,最完美的是大梵天。凡俗社會是滾滾紅塵,人只是臭皮囊。臭皮囊在紅塵當中苦海無邊,只有通過印度教的苦修冥想,才能達到大梵天的超凡的境界,進而得到解脫。
上述三大文明都是由外在超越的權(quán)威性存在主導凡俗世界,它們是二元論的世界。可是中華文明與這三個文明體系不一樣,中華文明認為最偉大的道理、最深刻的意義就在凡俗社會。人、天、大這三個字在甲骨文當中是同字,最早的甲骨文當中,人、天、大是根據(jù)語境區(qū)分的,但是其寫法基本是相同的。中華文明一開始就把人的成長、人的福祉作為文明的核心。中華文明的存在不是為了效忠上帝,不是為了凸顯大梵天的寬容和慈悲,不是為了證明理性的光芒,而是為了凡俗社會的美好和無限可能,所以中華文明是在紅塵中轉(zhuǎn)變紅塵,盡管這紅塵并不盡美盡善,可是中國人不把責任交給凈土、上帝或天上的理性,而是把責任放在自己身上。正因如此,它給人的品質(zhì)和精神的成長打開了一個無限的通道,它對社會可以變好寄予了無限的希望,人皆可為堯舜。每一個人通過自己的奮斗,都可以成為圣人。如果在基督教中有人說“人皆可為上帝”,這就屬于太大逆不道了,在伊斯蘭教中亦然。只有中華文明有這樣一個深刻的凡俗人文主義,所以,無論在法國,還是在美國,抑或是在中國講學,我一直概括認為這才是中華文明最核心的資源。
有些學者用“實用理性”來概括中國的文化特點,這是受康德哲學的局限,“純粹理性”、“實踐理性”的話語對中國學者影響太大,但其仍然是一個西方的話語。難道沒有西方話語,就講不了中華文明了?其實,中華文明有其最深刻的特點,即凡俗化的人文主義,它的人文主義不經(jīng)過宗教來體現(xiàn),不經(jīng)過任何外在超越的意識形態(tài)。“天人合一”、王道政治、經(jīng)世濟民的理念,全都是深深地扎根在凡俗社會,所以中國不能接受離開凡俗社會、離開日常生活、犧牲人民和犧牲社會而尋求的真理。中國不會圍繞一個外在超越的權(quán)威來建立自身的文明體系。
有一個非常有意思的例子:在哈佛有一個叫“文明對話”的學術(shù)活動,是杜維明教授推動的。一些中國學者、儒家學者和神學教授在這個平臺上相互對話。通過對話,他們了解了中華文明的一些核心要素和原則,非常激動——中華文明中居然存在那么深刻細膩的人文關(guān)懷,無論是猶太教,還是基督新教,都沒能達成這一點。所以,儒家文明與基督教文明并不沖突,基督徒完全可以接受儒家文明,成為一個儒家式的基督徒。需要注意的是,這個“儒家式的”是儒家成為形容詞,它不再是一個名詞,它可以用來定義某一種存在。然后,儒家學者與穆斯林的宗教神學家們討論,后者也認為儒家這一套理念非常有價值,其可以成為儒家式的穆斯林。儒家在穆斯林這里同樣可以成為形容詞。但是,基督徒的穆斯林,或者穆斯林的基督徒,就沒有出現(xiàn)過,因為基督教和伊斯蘭教在終極形而上學的存在是相互排斥的。信上帝就不能容納安拉,皈依安拉就不能侍奉上帝,終極形而上學的一元論一定會導致獨斷論。
在文明的發(fā)生學時代,中華文明沒有走二分的道路,留下了一條可以融合萬方的寬廣大道,這是我們的資源。有一次我就中國文化特質(zhì)的問題,請教錢鐘書先生,錢先生說了四個字:從善如流。我覺得這個概括非常好。中華文明不是一個宗教文明,不是以宗教教義作為最高法則的自我封閉體系,而是以人的存在為最深刻關(guān)懷的開放系統(tǒng)。只要能夠?qū)崿F(xiàn)人民的福祉,任何思想資源都是中華文明可以取而用之的。整個開放的過程體現(xiàn)了中華文明的精髓。如果中國人丟掉這個法寶,不再關(guān)心人民而專寵權(quán)貴,不再關(guān)懷凡俗社會而執(zhí)迷于教條原則,不再努力學習其他文明的優(yōu)秀資源而固步自封、自以為是,中華民族的生命力就萎縮了。
從善如流、向他者學習、變?nèi)藶榧骸⑺说馁Y源創(chuàng)造性地轉(zhuǎn)化為中華文明的資源,是漫長歷史上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的主要動力,中華文明曾經(jīng)花了上千年的時間消化印度宗教資源,極大豐富了自身。但現(xiàn)在的情況相當復雜,因為社會的物質(zhì)交融程度遠遠超過了精神交流的程度,這是我們這個時代最大的特點,由于交通的便利、人口流動規(guī)模的快速擴張、新信息交流手段的出現(xiàn),過去用幾百年來磨合的事情,現(xiàn)在一瞬間就在眼前,連一個思想文化層面上的磨合周期都很難準備。這是中華文明面對的新考驗,在某種程度上,這也部分引發(fā)了中國當代認同的困難和思想領(lǐng)域非理智的混亂沖突。
我舉另一個例子來檢討上述問題。絲綢之路開通以后,中華文明的很多特色和要素通過商隊傳入了阿拉伯世界,穆斯林世界的神學領(lǐng)袖和部落領(lǐng)袖們,對于中國這樣一個文明感到新鮮神奇。他們選派了自己的子女到中國來學習中華文明,這些孩子來的時候已是青少年了,還完全不會說中文,只能從頭開始學。他們在中原扎下來,研習儒家、道家的經(jīng)典,跟隨中國的理學家們,參與探討、辯論。最后,這批人成為伊斯蘭近代轉(zhuǎn)型重要的思想家。其中有個人,叫王岱輿,他也是青少年時期來到中國。他學習和消化儒學的精髓,然后由儒家精神返回去理解伊斯蘭教的經(jīng)典,真正形成偉大文明之間的雙向解讀。他寫了一本重要著作叫《天方性理》。“天方”是伊斯蘭世界的話語,《一千零一夜》里面涉及很多“天方”層面的內(nèi)容,“性理”是中國哲學的概念,尤其是宋明理學的核心范疇。他不僅向伊斯蘭世界展示中華文明,而且也對中國思想的形上超越提出疑問,至今讀來仍有價值。王岱輿不是個案,和他同來的還有其他人,且留下很多重要的作品和文獻。和西方傳教士進入中國帶著傳播基督教的明顯目的不同,他們完全是為學習理解而來,這是文明交流中的優(yōu)秀范例,讓那種文明征服、文化壓迫的文化殖民主義相形見絀,今天仍然值得倡導弘揚。
中華文明在過去漫長的歷史中,曾經(jīng)有過多次文明交匯和文明交融的經(jīng)歷,影響了世界其他文明的發(fā)展,這是中國曾經(jīng)的繁榮。但是今天碰到了很大的問題,中國受西方近代文明的影響太大、太快,其中有積極因素,但也不乏負面糟粕,如何從中展開創(chuàng)造轉(zhuǎn)化?甚至于可供轉(zhuǎn)化的時間都非常局促。更主要的問題是很多現(xiàn)實問題比文化問題更緊迫,所以我能夠理解中國的精英和領(lǐng)導們,幾乎每天都在處理非常現(xiàn)實、非常緊迫的問題,后面大的文化問題的關(guān)懷,缺乏必要的張力和空間、時間去深入推進。在這一情況下,我們該如何推進文明復興和價值重建?限于篇幅,筆者將另文探討此一問題。
本文系根據(jù)黃萬盛的長篇演講錄《價值關(guān)懷和民族復興》擇取編輯而成。
(作者系哈佛大學燕京學社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