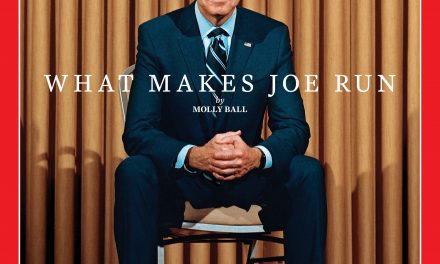阿富汗變局:
改變世界與改變歷史的重大事件
2021年最大的國際政治變局,當屬阿富汗事變。其帶來的戰略影響,將是長期的,其對于國際政治格局的影響,也是全局性的。
▍阿富汗事變是美國走向衰敗的標志性事件
近現代歷史上,美國也曾屢次陷入戰爭泥潭,敗在弱小國家手中,但美國在阿富汗的失敗,則是美國首次面對一個背后缺乏大國支持的小國對手的失敗。其中的含意是十分深刻的。它預示著,當代帝國主義霸權國家任意侵略并蹂躪弱小國家的時代已經過去,美國已經無力左右一個弱小國家內部的國家民族事務,無力將自己的意志強加于他國的人民。更何況美國這次是以北約的名義,動員了幾十個盟友的軍事、政治力量,最終卻落得倉皇而逃的敗局。
自冷戰結束以來,美國欲構建單極霸權的美國世紀,它四處干涉,窮兵黷武,以人權和反恐為名,不斷侵略、打壓他國。但不出多年,美國的衰敗之勢便開始顯現,其內政和外交不斷顯示出帝國末期治理失敗的種種征兆。2008年以來,陸續發生了三個美國步入衰敗下行臺階的標志性事件:
一是自美國而發,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機,其后遺癥迄今尚未治愈,其對美國經濟社會的傷害是根本性的,它標志著美國財政經濟金融體系的治理衰敗。
二是起自2020年初的新冠肺炎疫情危機,疫情肆虐下,美國迄今已有超4000萬人感染,69萬人死亡,這是美國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的失敗,在事關美國人民生命安全的根本性問題上,美國的體制機制與美國統治階級的能力發生了致命的紊亂和失靈,疫情危機證明,美國病了,而且病得不輕。
三是阿富汗事變,暴露出美國在重大國際政治沖突事件中戰略能力的下降,它的戰略規劃、戰略執行及戰略收尾各個環節混亂失效。其文職與軍職部門之間、各個部門之間、美國與盟友之間缺乏協調,組織能力明顯不足,標志著美國國際治理與國際統治能力的衰敗。
從阿富汗撤軍,表面上看是美國國家戰略的理智選擇,它需要在阿富汗快速止血,避免無謂的資源損耗,而將主要戰略方向轉向印太地區,集中精力應對中國-俄羅斯這兩個大國競爭對手。但阿富汗潰敗的實際效果,卻產生了對美國極其不利的連鎖反應,它非但沒有生成美國集中戰略資源與大國對手競爭的有利格局,反而大幅度削弱了美國的戰略資源汲取能力,動搖了美國可加利用的戰略資源的基礎。在歐洲方面,美國的北約盟友會由于阿富汗敗局而加速推動歐洲戰略的自主性;在中東阿拉伯地區,伊斯蘭反美力量會倍加鼓舞,通過各種形式的反美運動動搖美國在中東的基本盤;在東南亞等地區,苦于美國逼迫必須在中美競爭中選邊站的各國,會毫不猶豫地堅持獨立的國家政策;而在東亞地區與東歐地區的美國盟國,則會開始掂量美國作為盟友的可靠性,為自己的未來安全做一份新的安排和打算。
這些重要的心理變化,正日漸伴隨阿富汗事變而不斷反映出來,其實際效果就是大大削弱了美國霸權體系的資源匯集能力,大大增加了美國對手的信心。這一減一增之間,阿富汗事變對美國霸權損害的含意不言自明。
▍深刻認識當代伊斯蘭世界
阿富汗事變,給予中國人的最大震動,是塔利班這一傳統印象中“保守落后野蠻”的政教合一組織,竟然展現出如此強大的組織能力。為此,我們需要擺脫西方話語迷霧,深刻認識塔利班,深刻認識伊斯蘭。
衡量一個國家的真實實力,可有各種計算方法,現代社會更多地將物質力、科技力作為實力計算的基礎。但塔利班的勝利讓我們看到,一個國家的精神力與組織力才是首要的能力,精神信念的瓦解與組織能力的渙散,才是最可憂慮的。而恰恰在這一方面,今天我們的社會面臨著極大的隱患。
預判阿富汗未來的走勢,并在此基礎上制定相應的策略,可有各種參考因素,但有兩點,卻是研判當今阿富汗問題的最大前提:一是阿富汗經歷了40多年的戰亂,人民渴望和平與安定,這是阿富汗任何政黨、任何組織都不能忽視的基本民情;二是阿富汗存在著一個強大的組織力量——塔利班,這個組織經歷了近20年殘酷的反侵略戰爭,經歷了它第一個執政周期失敗的經驗教訓,在對內對外政策方面都日漸成熟。
認識阿富汗,認識伊斯蘭,中國人應該從西方媒體制造的話語迷霧中擺脫出來,避免簡單地透過西方的棱鏡去看被扭曲的真實的阿富汗。自從工業革命以來,伊斯蘭世界與中國等古老東方文明體共同面對著西方現代性的挑戰。近兩百年來,伊斯蘭文明與伊斯蘭國家,經歷了比中華文明還要艱難曲折的現代化建國之路。以阿富汗為例,它嘗試過西方經典資本主義現代化發展模式,也嘗試過蘇聯式的社會主義現代化發展模式,但最終都失敗了。古老的部落-家族社會、碎片化的民族構成、近代以來日益分裂的城鄉二元經濟社會結構、以及外部帝國主義大國的不斷干涉,都導致阿富汗的現代化之路顛沛坎坷,從一個失敗走向另一個失敗。
作為一種由意識形態和信仰體系推動的社會運動,塔利班與中東、中亞等伊斯蘭國家的許多組織共享著同樣激進的價值觀,并共同以反抗美國帝國主義的侵略為使命,因此它們的行動不可能局限在一國一地,而必然會溢出民族國家邊境,向周邊地區和國家蔓延。對于這樣的“輸出革命”,周邊世俗化伊斯蘭國家當然會心存憂慮,中國也不能不對此有所防備。但觀察塔利班,一個重要的特征是,它正以重建阿富汗民族國家為目標,而非以“輸出革命”為當下目標。它正進入現代阿富汗國家的執政階段,成為阿富汗的執政黨。而一旦開始執政,塔利班秉持的伊斯蘭教法革命的意識形態,必然會遭遇“革命與執政”、“一國與世界”、“教義與現實”等多重矛盾,并被迫不斷進行調適,以逐漸找到與現實世界相協調的治國姿態。
阿富汗事變發生的最大時代背景,是中美戰略競爭正上升為世界的主要矛盾,而中國的最終獲勝,取決于廣泛的國際統一戰線。為此,中國人需要深刻認識當代伊斯蘭世界,把握其中代表未來的革命性因素,并由此為中華文明的偉大復興做出正確的戰略選擇。
—?2021年10月新刊目錄??—
▍域外
迷霧:阿富汗之變
宛程
后默克爾時代德國對華政策的挑戰
胡海娜
▍封面選題:全面競爭
拜登執政后的種種跡象表明,以中國為主要戰略競爭對手,已成為美國主流政治精英思考中國問題時的基調與共識。中美之間的沖突,并不是爭奪霸權的“大國競爭”,而是由美國力圖壓制中國獨立自主發展引起的霸權與反霸權之爭。考慮到美國仍然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和國際秩序的主導者,無論我們的意愿為何,中國都將不得不面對這場競爭。至于能否在這場競爭中繼續自身的發展,能否將競爭導向良性的方向,則部分取決于我們能否客觀全面地認識美國的政策、戰略與行事邏輯。
貿易與人權(上)——世界帝國與“美國行為的根源”
強世功
“創造性破壞”與“墊背陷阱”——美國的性質與中國的應對
趙鼎新
全面戰略競爭:美國對華戰略新定位
張蘊嶺 孫志強
中美關系發生質變了嗎?——基于海量媒體數據的定量考察
高劍波 胡啟月 劉 彬?鐘飛騰 陳定定
▍世界觀
多極化時代的大國責任:不結盟運動的歷史啟示
孫歌
不結盟運動并非意在對抗歐美,它嘗試著走出一條多元化的人類發展道路。時隔大半個世紀,今天的世界看上去仍然霸權當道,當年的弱小國家各自經歷了內外變化,執政者也不再是當年那一代倡導不結盟的政治家;然而不結盟的理念卻宛如一條潛流,依然活在歷史的水脈當中。在所謂的新冷戰時期,如果我們轉換強國操控世界的思路,那么,新的世界史圖譜將呈現在眼前。
▍城市政治經濟學
廣深“雙引擎”:珠三角經濟生態圈的崛起與升級
張翔 蔣余浩
改革開放四十余年來,珠江三角洲經濟發展的明顯特點是形成了廣州和深圳兩個引擎。隨著港澳地區與珠三角地區的經濟融合日趨加深,今天珠三角地區已經整合在大灣區的發展范疇之中,兩個城市的產業形態也有了較大差異。
▍焦點
???
數字財富鴻溝:數字控制與資本控制的疊加效應
沙燁
在技術的支持下,數字平臺對財富形成“虹吸效應”,大大加快了社會財富的集中度,并放大了當前財富分配機制的缺陷,使各階層之間的財富鴻溝越來越深。
▍青年與青年價值觀??
小粉紅的系譜、生態與中國青年的未來
余亮
小粉紅是一個過程,它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寂靜的個人主義與“去政治化的政治”,重新接納了集體、國族、歷史主義、社會主義等維度。面向未來的問題是:生當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時代,粉紅一代究竟是會發展為崛起的一代還是淪為迷茫的一代?
偏離的飯圈——資本與輿論之間的網絡社群
金方廷
▍社會結構變遷
中國小農現代轉型的限制與出路
譚同學
在第二、三產業無法讓被能人和大戶排擠出的小農有尊嚴地實現人口再生產的情況下,“小農終結論”硬要消滅小農,即便可以制造出少量富有的農場主,整體上卻是一條兇險之路。若中國不想永久放棄農業現代化的戰略目標,“小農維持論”顯然過于保守。尤其在世界農業現代化加速的背景下,即便甘于守成,也是注定難以守得住的。新型農民合作或許既能容下小農的主體性,同時又可兼顧農業現代化,但它面臨合作難的問題,亟待從根本上加以解決。
▍重述世界史
帝國科學與帝國統治:發展話語的國際旅程
陳雪飛
▍歷史觀??
開國70年:中國復興的歷史觀察
胡傳勝
中國當代的復興,與前幾次都不同。20年前特別是30年前,復興的意識是不存在的。雖然“振興中華”是近代以來所有知識與政治精英的口號,但真正的復興意識,建立在對中國歷史同一性自覺基礎上的復興意識、強大意識,的確是近十來年的事情。與歷史上的五次復興相比,這次復興是真正的世界范圍的,其意義與影響也只有在世界歷史過程中才能夠說明
中華文明何以五千年不斷流?——一種歷史唯物主義解釋
王凱歌
本文為《文化縱橫》2021年第5期新刊手記,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系本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