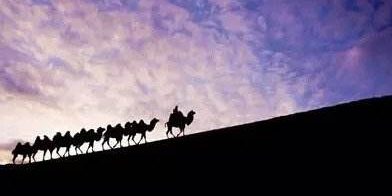王 柯
2014年是中日甲午戰爭爆發120周年。在這120年間,前半是以侵略與反侵略為主題,后半圍繞是以應該尊重歷史還是應該集體失憶,中日兩國之間的民族主義幾乎一直發生著沖突。然而不同的是,中國的反日民族主義很大程度上是在日本的教育和刺激下成長起來的,這是一個在評論兩國民族主義的性質時不可忽視的前后順序。
筆者一向認為,在理解近代中國政治歷程的問題上,有兩個不可或缺的視點。其一是中國進入近代國家之前最后一個王朝的最高統治階層不是漢民族,另一是中國清末民初的許多革命家和思想家都是通過日本(而并非通過其他國家)接受了建設近代國家思想的影響。這兩點并不相互孤立,而是有著緊密的內在聯系:革命家對于清王朝的“民族”歧視政策的反感和反抗,最終演變為“驅除韃虜,回復中華”的“民族”革命,而這個以建立“民族國家”為目標的“民族”革命的理論,恰恰是從鼓吹單一民族國家思想的近代日本學到的。從梁啟超在日本學到“民族主義”這個詞匯的那一天起,中國人的原初的淳樸的民族主義就與建設近代國家和新型“國民”聯系在了一起;然而,作為老師的日本,卻將民族主義和民族國家思想變成了動員煽動國民參加侵略戰爭的工具,近代中日兩國關系因此成為兩個民族國家之間民族主義激烈對抗的舞臺。所以,認識中國近代對外民族主義的產生和發展過程,首先應該按照時代在中日近代關系的層面上對它進行梳理。
中國的海洋意識與甲午戰爭
1840年鴉片戰爭的戰敗,迫使清王朝與英國之間簽訂了不平等的《南京條約》。然而即使割地賠款,此時的清王朝依然擺出一副“以不變對萬變”的架勢,自我陶醉于傳統的“天朝”體制之中。與此相反,沒有被中國人接受的魏源的“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思想卻在日本引起了強烈反響,日本人從鴉片戰爭中得到教訓,開始注意到“洋學”的價值。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中再次戰敗的清王朝,到了1860年代才終于進行“洋務”。洋務運動邁出了中國近代“自救自強”的第一步,然而它的視野里有的只不過是“堅船利炮”,實行“中體西用”的目的依然是為了維持傳統的社會結構和“天朝”秩序。而日本在1850年代即從“鎖國”轉向“開國”,1860年代開始對國家政治體制進行徹底的改造,經過“討幕運動”、“大政奉還”等確立了以三權分立制為基礎的中央集權制,之后再推行“四民平等”、“改正地租”、“殖產興業”、“文明開化”等各項具有實質性的政策,一步一個腳印地開始了國家近代化的進程。隨著國力的不斷增強,在中國人還沒有意識到近代民族主義之際,日本的民族主義已經開始膨脹,并且很快達到了1874年的“出兵臺灣”、開始鼓勵進行對外擴張的地步。
“出兵臺灣”是近代日本第一次出兵海外,也是“最初的踐踏清朝主權的事件”。它說明,日本民族主義的膨脹必然導致日本向外進行軍事侵略擴張,而其侵略擴張的矛頭首先就會指向以中國為中心建立起來的傳統東亞地區國際秩序。昔日的學生變成今日的強敵,日本的侵略極大地刺激了清王朝。然而由于內外交困,清政府內部出現了“海防塞防之爭”:塞防論主張收復在1860年代的穆斯林起義中丟失的對新疆地區的統治權,海防論則主張放棄新疆地區而把收復新疆的預算用到充實海防力量中。其實,不論是塞防派還是海防派,其代表性人物都是清朝內部的洋務派人物,二者都看到了近代帝國主義侵略的危險,不同的只是,應該把哪個國家視為最危險的帝國主義,然后將這個假想敵可能來侵的方向列為國家的防衛重點而已。“收復新疆”的背后,隱藏著是否應該將俄國作為一個最危險的假想敵。
表面上看來,“塞防論”的勝利似乎說明此時的清朝政府還沒有將日本看作是最危險的敵人,然而更根本的原因,恐怕還是因為清朝政府沒有擺脫中國以萬里長城為象征的“重陸輕海”的傳統國防思想的思維。關于近代中國衰退的原因,人們常常列舉清王朝統治階層的腐敗、保守與自大,然而卻常常忽視了一個重要的原因:無論是統治階層還是知識精英,都在國家經營的層次上缺乏海洋意識。
古老的中華文明是一個大陸文明,在中國的文明體系里,海洋從來沒有占據過重要的位置。作為一個經濟完全可以自給自足的大國,中國人更愿意把從海上來的人們都看作是來“天朝”的“朝貢使”。作為一個農業文明共同體,中國如何抵御游牧民族—“胡人”的入侵,才是真正令歷代王朝統治者頭痛的問題。所以,能夠在西北建造起雄偉的“萬里長城”,卻從沒有一個王朝想到要東南去建設一支海軍力量。明王朝為了杜絕倭寇,想到的方法只是嚴格實行海禁政策;而終于跨過萬里長城統治了全中國的清王朝,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中國人傳統的“華夷思想”,但對中國以及北方民族政治傳統的繼承,中國傳統的防衛思想進一步發酵:在內陸方面雖然屢建“武功”并進一步明確了國家的主權范圍,但在海洋發展的方面卻顯得更加慎重,斷斷續續地實行以海禁,延續著鎖國政策。
但在英國工業革命之后,列強各國為了在海外獲取殖民地和擴大勢力范圍,爭相加強海軍力量成為近代國家主要的軍事和防務思想。日本進攻臺灣以后,清朝也建立了“水師”,但水師海軍建設一直阻礙重重。而在這期間日本的海軍力量終于凌駕于中國水師之上,從而在1894年的甲午戰爭中大敗清朝。甲午戰爭是“中日關系發生質變”的標志,更成為讓中國人重新認識海洋、重視海上防務力量的契機。甲午戰爭的結果長期影響到中日關系的方方面面,近年來中國要成為海洋大國、加強海軍力量的聲音不斷高漲,其背景上依然可以看到有對甲午戰爭給予中日關系之影響進行深刻反省的原因。
近代中國自我認識的三階段:對外民族主義的生成與發展
對中國人來說,敗給日本比敗給西洋列強各國在精神上的打擊更加沉重;中國突然轉為向昔日學生的小國日本“割地賠款”,尤其是給知識分子帶來了強烈的恥辱感。1895年4月《馬關條約》簽訂后,5月里在北京的1300名舉子在康有為的率領下“公車上書”,揭開了戊戌變法運動的序幕。
鴉片戰爭之后,中國也發生過許多“攘夷”的運動,但那只是在對國際社會和國際關系缺乏充分認識的情況下,“住民們在對外部侵入者感覺到了危險時所產生的本能的行動。”但是《馬關條約》簽訂后的“公車上書”,卻是由近代中國知識分子所發動的第一次政治請愿運動,它是中國的知識分子開始作為一個社會集團站到了民族前線的標志。孫中山也于1894年在夏威夷組織起了以打倒清政府為目標的“興中會”來發動革命運動。但是不管是變法派還是革命派,雖然他們的行動方式和最終目的有所不同,但從國際社會的局勢變化后深感中國面臨深刻危機而認為必須尋求中國的政治體制變革的思路上來看,二者的性質卻是相同的。
梁啟超認為,近代中國及中國人的變革和進步往往是從認識到了自身不足而開始的。首先是“器物不足”,然后是“體制不足”,最后是“文化不足”。應該注意到的是,而后兩次變革的發生都是與中日關系分不開的。為了解決在“器物”方面的不足,洋務派只是進行了“利器”(建設新型工業)、“練兵”(創建新式軍隊)、“興學”(導入新式教育)等實質性的嘗試。但是要進行體制的變革,是要以否定以中國為中心的“中華世界”的傳統世界觀為前提的,因此不得不說戊戌變法是中國自我認識過程中的一個革命性的事件。而戊戌變法是由甲午戰爭的戰敗而起的,由此就可以看出甲午戰爭給中國民眾造成了多大的心理沖擊。
從1884年到1914年之間,日本一共參與了三次戰爭(甲午戰爭、日俄戰爭和第一次世界大戰)。而對日本來說,這三次戰爭不是以中國為敵就是以中國為戰場,并且借機從中國獲取了大量的權益。日本對中國的侵略,在1915年時以提出對華二十一條而達到了新的地步。以此為背景,中國人民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民族意識也一舉高漲。二十一條簽訂的5月7日、5月9日被中國民眾視為“國恥紀念日”,從1915年開始一直持續到1921年的抵制日貨運動成為民國以來首次全國性的民族運動,也是中國經濟史上歷時最久的抵制外貨運動。1915年9月以《新青年》雜志的創刊為標志而開始的新文化運動,開始對傳統文化進行再評價,在因中華民國的成立而完成了體制革命的基礎上,開始了近代中國和中國人自我認識的第三個階段。
1921年中國共產黨的建黨,是以近代中國和中國民眾的民族主義的覺醒為基礎的。關于這一點,可以參考葉嘉熾所做出的如下分析:“由于向西方國家爭回國家主權的奮斗屢遭挫敗而產生的一種痛苦的覺醒,不時的咬嚙著知識分子的心靈,他們對科學精神雖樹起了信念,然而對產生科學精神的西方國家喪失了信心。同時,他們又不愿在回到東方的傳統中來,于是有些人竟投向所謂現代的、科學的、包容一切的、反西方的馬克思主義”。
就這樣,隨著日本對中國侵略的加劇,中國民眾尤其是知識階層對國土分割和民族滅亡的危機感、對內建設近代國家和對外維持國家獨立的緊迫感不斷被強化,近代中國的對外民族主義也就隨著中日之間的甲午戰爭而問世、又因肆無忌憚地踐踏中國主權的對華二十一條而發展到了新的階段。
近代中國的“尊王攘夷運動”
戰爭經驗所帶來的結果,并不僅僅只反映在國家的層面。直到1920年代,中國的民族主義主要停留在知識階層,而九一八事變以后日本對中國不斷升級的軍事侵略,由于其受害者范圍之廣,則成為了對中國社會的廣大民眾進行民族主義思想和體驗之教育的最好教員。
我們常常以為中日戰爭就是“八年抗戰”,這是從中國軍隊開始正式的抵抗的時間點(1937年7月7日的盧溝橋事變)進行計算。但是在日本,對當年日本侵華具有反省意識的學者中有不少人認同“中日十五年戰爭”之說,就是說日本對中國的軍事侵略應該從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算起,而且這個“中日十五年戰爭”就是“以中華民族本身為敵”的戰爭。例如731部隊將中國人作為細菌武器試驗工具,就是視中國人生命如草芥的證明。有日本學者揭露,由天皇直屬的最高統帥部大本營的參謀總長——載仁親王(皇族)曾親自對北支那方面軍司令官杉山元下達使用化學武器的命令:“根據大陸命令第二四一號做出如下指示:1,北支那方面軍司令官在其占領地區內的作戰中使用芥子氣(黃劑等特種資材)并研究其作戰上的價值”,但同時又提出:“采取萬般措施以隱匿事實,尤其是對第三國人絕不能傷害,同時要絕對對他們隱匿事實。”這也說明,上至皇族、下至“皇軍”,普遍具有對中國民眾進行民族屠殺無罪的思想。因此,掛著“皇軍”名義的日本軍隊敢于屠殺中國人,而這種民族屠殺又自然刺激了中國民眾的仇日反日的民族意識。
1937年1月2日,在北京創辦崇貞學院的清水安三帶著夫人等,6名日本人一起拜訪了當時的北京大學教授胡適。應日本來客的要求,胡適在名片上寫下了“尊王攘夷”四個字相贈,而這讓日本來客們感到非常不安。盧溝橋事變前的中國社會,可以說與“尊王攘夷”運動時的日本社會形勢十分相似,一方面是國內各個政治勢力之間分裂對抗,而另一方面又面對著外國、主要是日本的侵略勢力。然而,胡適之所以給來訪的日本客人贈送“尊王攘夷”四字應該還有一番深意:盡管中國國內各個政治勢力、軍事勢力之間明爭暗斗,各個地域、社會階層之間分裂對立,但是中國人在對內處理“尊王”問題的同時,也不會忘記還有一個要對外一致“攘夷”的重大問題。
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幫助中國民眾認清了日本的侵略目的。但是圍繞“攘”的方法和“尊”的對象,國內各政黨、階層、集團依然存在深刻的對立。以胡適為代表的一部分自由派知識分子曾經認為:因為中國軍隊武器裝備落后,中國的軍力難以與日本相比。所以輕言抗戰的豪言壯語將招致亡國,故而他們反對輕易對日宣戰。但是隨著日本對中國侵略規模的不斷擴大,從1932年的淞滬抗戰到1936年的西安事變,一連串的抗日呼聲,證明中國民眾在面臨民族存亡之時,表現出了“中華民族空前的覺醒”。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時,陸軍大臣杉山元在給天皇的上奏中狂言:“一個月之內解決支那事變”,但是在短時間內征服中國的美夢很快落空。面對日本的瘋狂侵略,國人表現出了“必死的民族抵抗”。事變發生之后,中國共產黨表明態度愿意接受國民政府的領導。在民族大義面前,各個黨派勢力拋棄前嫌,結成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八年抗戰”因此也變成了胡適所說的中國近代的“尊王攘夷”、造就具有國家意識之國民的運動。
“同文同種”是一種鴉片
日本之所以對大陸野心大增和敢于最終發動侵略戰爭,是與明治維新以來推行近代化、實行富國強兵政策分不開的。而日本近代化的成果通過各種渠道、包括戰爭等手段直接刺激了中國近代國家思想的啟蒙。變法派以為中日兩國國情接近,認為日本的君主立憲制可以為清王朝所借鑒,因此將日本的明治維新作為了戊戌變法的模型。而革命派則學到了單一民族國家思想,這一想法又得到了抱著不可告人之目的的日本大陸浪人、以及政界和軍界的慫恿。長期對日本的政界及民間抱有極大期望的孫中山,將日本視為作為中國革命的根據地,一直期待通過聯合日本的力量,前期是為了實現中國革命,后期是為了對抗西方列強。他在1915年2月5日與日本民間人士間簽訂的“中日盟約”中承諾給予日本的利益,甚至都超過了對華二十一條的內容。
從1896年起,清國內出現了留學日本的熱潮。日本留學的興起和發展,其原因可以列舉出清朝政府的支持、日俄戰爭中日本的勝利(1904年)、中國科舉制度的廢除(1905年)以及圖謀通過接受清國留學生在大陸扶植親日勢力的日本矢野文雄公使向清朝發出的邀請等。但不論是哪一種理由,之所以能夠被中國民眾以及青年學子所接受,就是因為它與當時的中國人的日本觀中的“同文同種”的因素相通。
洋務派的張之洞在《勸學篇》中為其極力推薦中國青年選擇日本留學的理由作了充分說明,除了政治的考量之外,兩國地理、風俗尤其是文字之接近也是他用來打動人的地方。而在留學生自己的敘述當中,我們也能夠看到很多關于中日兩國“同文同種”的內容。然而,中國人對于中日兩國關系這種基于人種、文化上的主觀認識,實質上具有居高臨下看待日本和日本人的意味。因為在“同文同種”的想象中,日本人和日本文化都不過是在中國人和中國文化的延長線上成立的。這種意識或者事實關系,在中國為東亞地區的中心時進行強調當然不會有任何問題,但是在日本產生侵略大陸野心時自然要成為他們的絆腳石。
當然在日本,也有像巖倉具視、樽井藤吉那樣從“同文同種”的意識出發,提倡日清或者日清朝(鮮)建立同盟關系的人物。但是幕府末期以來所謂唇亡齒寒的東洋同盟論,比起“同種”的意識來,更加重視的還是地理上的兩國或三國之間的唇齒相依關系,其收益的目的還是為了阻止歐洲列強對亞洲的入侵。福澤諭吉就是在看到東亞各國不能進行國內改革,因此無法與西洋列強抗衡的前提下,看出了對于日本來說其他亞洲國家已經無用,于1885年發表了《脫亞論》的。因為將一切為了日本當作唯一的目的,福澤諭吉的脫亞論,其實從最初就為日本定下了將亞洲變為日本殖民地的方向。
與中國人更希望把中日兩國的關系放到人種和文化的聯系中去理解相比,近代日本其實最初就是把兩國關系放到地緣政治、國際政治的角度來考慮的。即使有部分日本人一度想到過的亞洲團結,最終也不過是日本的亞洲政策和對華政策的上述終極目標下的一顆棋子。在如何認識兩國之間關系的問題上,中日兩國之間其實存在著巨大的差距。例如,日本社會中全心全意地真正支持孫中山進行革命活動的,僅限于以宮崎滔天為代表的個別“中國浪人”;而孫中山卻不分朝野一直追求與日本的聯合,直到1919年才開始了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批判。
然而,變法運動也好,民族革命也好,日本留學也好,不論哪一個其實都是在證明首先接受了西歐價值的日本的優越性,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日本人的中國觀也逐漸從崇拜轉為蔑視。“禿子頭的李鴻章,最后變成了禿和尚”,這個俗語很好地詮釋了當時日本人看待中國人的心理,甲午戰爭之后,在日本社會里作為一種蔑稱的“清國奴”開始普遍流行。生活在日本社會中的清國留學生,對此最為敏感。“在留學生中之所以反日人士層出不窮,就是因為在他們的對日觀中,加入了留學生活的實際體驗,從而使日本作為帝國主義的形象被擴大了。”(『近代中日關系史料』第Ⅱ集,)。事實證明,在日本原本希望培植成在大陸的親日勢力的清國留學生中,有許多人日后反而變成了反日民族主義的先鋒。
最大的悲劇就在于,日本人事實上在福澤諭吉的時代就已經拋棄了“同文同種”的思想,而對于中國人來說卻一直難以舍棄“同文同種”的幻覺。從孫中山、蔣介石一直到共產黨,“同文同種”的意識一直都活在歷代的對日關系中。蔣介石即便是在抗日戰爭期間都會反復向國民訴說日中兩國原本同文同種,本應互相提攜成為友好鄰邦;中國共產黨的評論家,也在1937年抗日戰爭開始以后依然強調中日兩國原是同文同種。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徐福傳說”越傳越廣,甚至還在“下海”之處建起了徐福廟,包括許多對日本抱有成見的國民也樂此不疲地通過“徐福傳說”對“日本人本是中國人的后裔”一說進行求證。
對于中國人來說,“同文同種”的思想就像是一種自我陶醉、自我麻醉的鴉片。然而可怕的是,這種鴉片會帶來劇烈的副作用:越要說明自己在民族上和文化上的優越性,就越想證明日本與中國為“同文同種”;但是由于日本拒絕這一包含中國是日本人和日本文化祖國意味的思想,想證明“同文同種”的愿望越強烈換來的失望感也就越強。于是,在這樣一種“同文同種”的語境中,能夠出現的因素就只有中國的強烈“期待”和日本的極大“背叛”,而結果也只能是激起中國民眾的極大憤怒。不得不承認,“同文同種”這個鴉片制造出來的幻覺,在以對抗反抗日益膨脹的日本侵略主義的民族主義為背景的近代中國的民族主義形成和發展過程中,一直發揮了迷惑中國人的興奮劑的作用。
不斷為現代中國民族主義提供溫床的日本
費正清曾經指出:中國人是一個“非常看重歷史的民族”。毫無疑問,今日中國的民族主義思想的背景上,的確有清算近代史上所遭受的恥辱的歷史成分。但是,這種強烈的歷史恥辱感之形成,與以侵略中國為背景的日本民族主義的膨脹之間具有直接的關系;而時至今日日本的政治家和日本社會中所存在的根深蒂固、不斷蔓延的否定侵略歷史的言行,又是不斷刺激中國反日民族主義膨脹的原因。
毫無疑問,近代民族主義是一把雙刃劍。在對抗侵略的過程中民族主義無疑可以發揮重要的作用,然而在和平時代它就有可能變成威脅社會穩定和再次把國家和國民推到戰爭邊緣的因子。在國際合作變得越來越重要的今天,如果還要把它當做是民族國家發展最高的唯一價值,就無異于是把自己從國際社會中孤立出去。而今天,對經濟聯系已經達到了可謂生死與共地步的中日兩國來說,只有建立起和平友好的中日關系才能利人利己。所以不論是在哪個層次上,民族主義的影響都應該得到適當的控制。然而,從以上的分析中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與被侵略的歷史同步發展起來的中國人的民族主義,本身就是一個被動型的民族主義。因此,控制中國民族主義使其不再膨脹的關鍵不在于中國自身,而在于有沒有受到外部侵略以及會不會否認那段侵略過中國、并給中國民眾造成了巨大創傷的歷史。
但是遺憾的是,今天仍然不停地揭開那塊傷疤的,是日本的一部分政治家,而不是中國人自己。諳熟投票政治游戲規則的日本政治家們為了利用民眾的民族主義心理,接二連三地否定侵略中國的歷史,拿到了政權的政治家們則沉溺于玩弄國際政治的文字游戲:嘴上說著“并不否認給亞洲各國國民帶來了痛苦經驗的歷史”,行動上卻質疑村山談話,質疑河野談話,質疑東京審判,甚至公然以政府首腦身份參拜供奉著對各國人民犯下滔天罪行的A級戰犯的靖國神社。這些言行,對于一個著重歷史型的、被動型的民族主義來說,當然就是一種非常強烈的刺激。因此不得不說:當年中國對外民族主義的誕生和發展就與日本民族主義的教育和刺激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而在今天這樣一些政治家的手中,日本依舊是一個不斷地向中國的對外民族主義提供著發酵條件的溫床。
(作者單位:日本神戶大學)